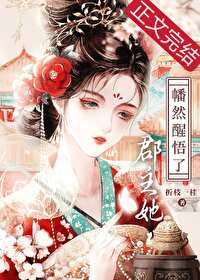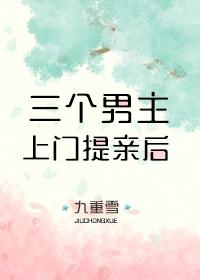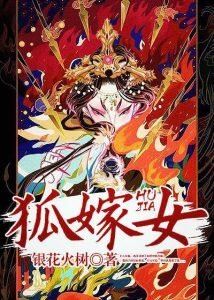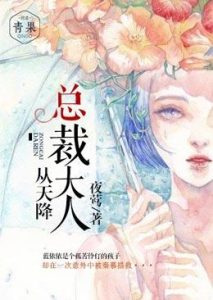明月 3
沈浪是誰?
他是“九州王”沈天君的獨子,來自傳承了百年的武林世家。“九州王”沈天君是那時的天下第一人,連雲夢仙子都不是他的對手,到最後他也是死于自盡。
柴玉關與雲夢仙子設下毒計,以百年前無敵和尚留下的《無敵寶鑒》為誘餌,吸引天下高手來到黃山,引起他們的争鬥,自己借着“萬家生佛”的美名得到這些高手留下的武功秘籍,一場腥風血雨,連沈天君都卷入其中,不能例外,可等沈天君趕到所謂的藏寶之地,只看到柴玉關留下的一句“諸位上當了”。
想到那麽多人為了所謂的“無敵”而死,終究是一場空,沈天君悲憤中選擇了自盡。
父親死後,那時不過十歲的沈浪将家族積攢了百年的財産全部散去,獨自浪跡江湖,直到尋找到了當年設下毒計的元兇:已經在關外成為“快活王”的柴玉關。
同樣背負家仇,年輕時沈浪倒是和傅紅雪有着微妙的相似之處,尤其在感情上,他們都不敢在前途未蔔的情況下接受這份愛意,沈浪越是在意,越是冷漠,傅紅雪越是動心,越是抗拒,他們都一度将自己深愛的人徹底推開。
只是比起傅紅雪面對帶着“丈夫”來的翠濃,終究忍不住失态,沈浪在面對另結婚約的朱七七時,卻不過是退了一步,呆立半晌,便又能做出一副灑脫的笑容來。
比起自幼浪跡江湖的沈浪,埋頭練刀、一心報仇的傅紅雪确實城府不深。
在沈清羽的記憶中,有一次王憐花喝多了酒,借着醉意說起往事。
年少時他心中只有扭曲的恨意,因為自己得不到幸福,便希望天底下所有人都痛苦,他故意和朱七七訂下婚約,再帶着她到沈浪面前,看着兩人一個裝得冷漠無情,一個裝得灑脫淡定,王憐花的心裏真是歡喜極了,因為他知道,他們兩個一定都很痛苦,他們覺得痛苦,并且會一直為此感到痛苦,這樣他就高興了。
彼時沈浪攬着已經喝醉的愛妻,笑着回答說:“但也是你,主動解除了和七七的婚約,我們始終都記得的。”
是啊,也是他主動解除了婚約,王憐花擡頭看着空中的明月。他和沈浪雖秉性完全相反,但有一點是一樣的,那就是他們的心思都很深,肺腑之言從不對人吐露,也只有時過境遷的今日,借着酒意才說起:“畢竟她也太可憐了,即便是我,也會想要成全她。”
兩鬓斑白的洛陽公子嗤笑道:“她的命實在不好,才滿心滿眼都是你,那時候,你對萍水相逢的姑娘,都比對她溫柔。”
多麽可憐的女孩,她本是無憂無慮的天下首富之女,白玉砌地、金粉鋪街也無不可,卻為了愛的人一頭紮進這風雲詭谲的江湖裏,一次次遭遇危險,幾番出生入死,可她得到的卻只有沈浪永遠若即若離的态度。
尤其是白飛飛幾次暗中設計,被蒙騙過去的沈浪責罵朱七七的莽撞任性,連她自己都覺得是自己闖了大禍。
若不是被傷透了心,愛得發狂,恨得也發狂,她又怎麽會情願死在沈浪手裏?
或許在選擇成全她的那一刻,王憐花早已被毒液浸泡透了的心裏,才真正有了些許對這個姑娘的憐愛。
就像憐愛那個渴求母親的慈愛,卻終究什麽都得不到的自己。
幼年的沈清羽當然不會覺得自己每日裏快樂活潑、好像永遠不會長大的母親有哪裏可憐,便也看不懂父親眼底複雜的情愫,不明白熊貓兒為何嘆息。
——————
一輪海上明月,兩地傷心故人。
顧绛透過沈清羽的記憶,看向面前的蒼白少年,他知道自己每換一次身體,都會在融入這個身體的同時被重塑,靈魂影響身體,身體也在影響靈魂,他就像一艘忒休斯之船,被不斷改變。
但他并不抗拒這種改變,人總是在變的,獲得別人留下的身軀,也被對方影響,這是他應該付出的代價,世間任何事都有代價。
朱七七如此,沈浪如此,王憐花如此,他顧绛也不例外。
而傅紅雪更是要為他的傳奇付出半生痛苦的代價。
在翠濃為他而死的時候,在經歷了這麽多之後卻被告知自己本與這一切無關時,甚至是在近二十年後,見到一張和翠濃相似的面容而痛苦到難以自制地發病時。
誠然,顧绛想要見識一下在極致的痛苦中練就的刀,但他只是驕傲自我,并不殘酷肆虐,也不打算放縱性情,失去自己為人的邊界。
他不會為了杜絕後患殺死任我行和向問天,不會因為已知的結局苛待任盈盈,拆散她和令狐沖,不會為了追求一場全力以赴的對決把風清揚逼入死境。
他也不會為了見識一種武功就去摧殘一個可憐、可敬的人。
何況任何道路的本質都是一種自求,而不是在別人身上尋找答案。
否則就是本末倒置,是人行邪道,不可見如來。
所以,顧绛願意成全傅紅雪,讓他從仇恨痛苦中解脫出來,也願意期待他在截然不同的人生中練就獨屬于他的刀。
公子羽喝完了這杯酒,終于決定起身離開,在站起來之前,他再一次向傅紅雪發出了邀請:“希望我們下一次再見時,你已經得償所願,一身輕松地願意來幫我。我自認為并不是一個惡劣的老板,會給做事的人發相應的工錢,而人都要吃飯,大俠也是要養家的。”
說完後,他沒有等傅紅雪再次開口拒絕,就登上了馬車離去。
——————
顧绛翻閱着手中的《天地交征陰陽大悲賦》,不得不說,雖然沒有傳說中那麽神奇,但《大悲賦》依舊是曠世絕學,而且這上面記載的七門武功都魔性極重,尋常人根本無法練成,即便是有天賦的習武之人,多半也只能練成一種,如多情子和花白鳳。
但顧绛練起《大悲賦》來,竟十分順利,他有練過邪門兒武學《葵花寶典》的經驗,經年鑽研《九陰》、《九陽》,對天地陰陽四字所學頗深,加上心性如此,這魔教自己都無人能全部練成的《大悲賦》倒似為他專門準備的一樣,進程一日千裏。
到了顧绛的境界,早就不再拘泥于招式,他所探究的是《大悲賦》中蘊含的武學思想和魔性真意,這七門武功雖然看起來邪異,但能達到這種詭谲的效果,背後也蘊含着極深的智慧。
顧绛在剛進入上個世界時,就游歷江湖,結合沈清羽這一年在中原的見聞,大致能摸清江湖正道傳承武學的兩種思路,一者重外功,一者重內勁,但無論是偏重一方,還是內外兼修,最重要的依舊是“中正”二字。
這不是平庸,而是一種大智慧,人生于自然,要打磨根基,得從強身健體開始,任何正道武學一定是能夠強身健體的,所以武功要和身體達成和諧,其秉性一定要中正。
像《葵花寶典》起手就要求動刀子,是非常典型的邪功,因為它損傷自身,扭曲天然心性。
人在天地間,武學的初衷是為了讓人更好地在自然環境中生存,弱者能以弱勝強,強者能夠自勝,随着人的智慧加深,無數前人在這條道路上越走越遠,它便成為了一種超出人體之外的大道。
《天地交征陰陽大悲賦》的立意極高,這從它的命名就能看出,天地交征,陰陽相生,這是萬事萬物發展的規律,人是順應這種規律而活的,可這門武功的精要就在于“大悲”二字。
“悲”者,非心,違逆心意則悲。
天地陰陽的輪轉亘古不變,這違背了我的心意,令人大悲,做下此賦。
關于《大悲賦》寫成時天雨血、鬼夜哭的傳說雖假,但這種要天地順我心意,我心意達成時天地當哭的氣魄不假。
若寫成此書的人是最初的魔教教主,便不難理解,他為什麽要将自己的教派命名為“魔教”。
中原本沒有“魔”這個字,是佛經東來後,翻譯的學者從梵語中譯出了這個字,原作“磨”,南北朝時梁武帝認為此字當從“鬼”,改成了“魔”。
如果佛是人人覺醒悟得的智慧,那魔就是人抵達這種智慧路上的障礙,它是欲望、惡念、執着、殺孽,是不能放下,不能順意,不能看透因果,不肯悲憫生靈,是在明知萬物皆歸大寂滅時,依舊不知天命的憤怒和狂妄,是在無邊苦海中不願回頭的行船。
魔會壞人修行,奪人慧果,造就無邊殺業。
我不行正道,不悟正法,不循天地之理,滿手血腥,殺人無數,我當為魔,我建立的教派,自然就該叫“魔教”。
寫下這本秘籍的人是這樣心性,他留下的武功如何可想而知。
其中的七門武功,處處違背常理,人的穴道可以移動,人的精氣可以剝奪,人的感官可以迷惑,人的思想可以篡改,化血為刀,抽骨為劍,死中蛻生。
江湖上當然也有許多類似的武功,但那些武功的出發點大多帶着對敵人的惡意,可這些武功的創造者字裏行間透露的是一種突破常理的快意,化不可能為可能的傲慢。
當發現這一點時,顧绛甚至有一種大笑的沖動,他從這些離經叛道的文字中,仿佛見到了那位不可一世的奇人。
多麽有意思的一個人?想到這世上曾有這樣一個人存在過,便足以令人大笑。
“可惜了,若我早一點通讀此書,應當去看一看他的墳墓,和他打個招呼。”顧绛難得如此開懷,甚至笑彎了一雙眼睛。
馬車裏正在沏茶的孩子好奇地看向他,但沒有開口說話,連端正的坐姿都沒有絲毫改變。
這個不過十歲的男孩是老管事挑選來作為公子羽的書童的,他的名字就叫“王書”,因為天生能過目不忘,負責為公子羽記事背書。
顧绛見他好奇,便将手中的《大悲賦》遞給了他:“這書中真意,說不出來,你自己看吧。”
王書雙手接過書冊,一看到封面上《天地交征陰陽大悲賦》九個字,竟雙手一顫,險些将書落在小桌上,文靜的小臉一片煞白,仿佛手裏拿的不再是一本書,而是一件塗滿劇毒的暗器,讓他打開也不是,放下也不是:“公子,這是絕頂秘籍,書童不敢窺視。”
顧绛看他吓到的樣子,搖了搖頭:“武功秘籍被寫下來,就是給人看的,若是不願教人知道的事,只會随着主人一起埋入黃土,你看就是了。”
東方不敗收集到的那些武功秘籍,也都随意地放在他的書架上,往來者若感興趣,就可以去翻看,只要不帶走導致遺失就行。
顧绛是從來不忌別人學會絕世武功的,他甚至希望江湖上能有十個百個的頂尖高手,每個人都能走出自己的武道,能讓自己在和他們的交手中更進一步。
王書咬着牙翻開了這本傳說中的絕學,漸漸的,他臉上的慎重、興奮、恐懼,就變成了迷惑、難以置信,最終定格在不以為然上,他年紀雖小,但能被選出來跟在公子羽身邊,當然是自幼就學了上乘武功的,而且他還好讀書,十歲上就對很多事有了自己的見解。
他覺得自己明白了公子笑的原因,因為這上面的武功并沒有傳說中的那麽厲害,公子在笑世人被欺騙了。
顧绛端起一杯沏好的茶,沒有說什麽,只望着車窗外。
四匹純白的駿馬拉着能工巧匠打造的馬車,車後挂着的兩只銀鈴在極速前進中也沒有發出聲響,以保證馬車的平穩,不讓車中人受一點颠簸。
大多數江湖中人見到這樣奢華的馬車,在驚嘆來人的財富外,都會不由自主地生起一種輕視,因為對方的張揚浮華,容易惹來麻煩,本能地覺得車中主人輕狂少智。
就像聽到浮誇傳聞後,第一眼見到《大悲賦》的人。
可王書會明白這本書的可怕,就像這座邊城的人,也會知道這馬車帶來的,是怎樣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