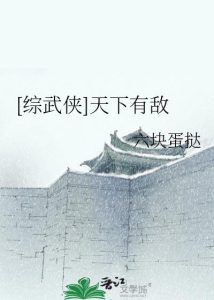道魔 3
忽必烈嘆了口氣,不再迂回敘述,直言道:“我今日見你的目的,小斑你應當心中有數。”
在自己壽數将盡時,提起昔年巴師八見成吉思汗的事,忽必烈想要在自己離去之前,将龐斑留在蒙元陣營中的意圖不言而喻,他既然說起巴師八,那就是願意許龐斑“國師”之位——以龐斑魔門出身的背景,屆時少不得被天下人叫一聲“魔師”。
巴師八會閉關圓寂,蒙赤行這些年也有大道将成的跡象,說不定哪一天就會棄世而去,在這個大宗師可以震懾天下,穩定一國的背景下,忽必烈不能不為子孫後代做打算,趁現在自己還活着,他和龐斑尚有同門之情,若等他逝去,以魔門素來的無情,龐斑可不見得會關照他的孫子鐵穆耳,更遑論後繼者。
其實,就算龐斑答應了做蒙古國師,他也不見得就會一直為蒙元效力,這點忽必烈看得很清,比起出身草原部落、骨子裏重情的蒙赤行,龐斑本是孤兒,他只對蒙赤行有感情,至于其後的蒙元、甚至是魔門,他都素來淡淡。
但忽必烈也不能做再多了,搭起這座橋梁,如何留住蒙師的繼承者,就看鐵穆耳自己的本事了。
龐斑也明白這一點:“我既然來見汗王,便是我對師父和汗王的回答。”
蒙赤行對蒙元的感情極深,他一生都在庇護鐵木真的子孫,龐斑承他養育之恩,願意應下這個職位,只是為了讓蒙赤行安心,讓他舍下最後的牽挂,徹底投入對天道的追尋中去。
對龐斑這樣做的原因,蒙赤行十分清楚。
大都是蒙元最繁華的城市,高武背景下這裏的民風悍勇,精力旺盛,入夜不息,猶自喧嚣騰騰,帝師府邸內卻一片清寂,府上沒有家丁護衛,只有管事和幾個做雜事的仆役,他們要做的事情不少,這個時候已經早早睡下了。
身披綢緞披風的少年提着琉璃燒制、珠寶鑲嵌的小燈慢悠悠從門外踱進來。
蒙元皇室極為奢侈,好聲色、犬馬、豪宴,忽必烈晚間在宮中設宴慶祝,為龐斑引見明孝太子真金的第三子鐵穆耳,也就是忽必烈現在的皇太子,他身後的繼任者。
宴上的美酒成池,肉食成山,魔門出身的美人揮袖如雲,絲竹靡靡,甚至帶着些陰癸派天魔秘法的影子。
自陰癸派的首領血手厲工追尋無上宗師令東來的去向,一去不回後,魔門內陰癸派一脈因厲工的師妹符瑤紅自立門戶而勢弱,也不知這些女子是陰癸派之人,還是天命教的。
看了一場暗潮湧動的宴會,新任的蒙古國師被忽必烈安排馬車送回府上,車夫還為他披上了風衣、遞給他一盞提燈照明。
龐斑側耳靜聽了片刻,提着這盞精工奇巧的無骨燈向蒙赤行的書房走去,果然見到熟悉的身影倚在廊前,看着一棵梧桐,風吹動樹葉簌簌,松動的葉子半黃,将落未落。
蒙赤行在他踏入府門時,就知道自己的小徒弟回來了,他沖龐斑招了招手,讓少年在他身邊坐下:“今夜的宴會,你覺得有趣嗎?”
龐斑笑了笑,眸光流轉,一身道韻悠長中終于顯露出了魔念的冰冷:“無甚意思,若是師兄的子孫不改此奢靡之風,任由合歡之術在宮中盛行,蒙元的國祚絕難長久。”
蒙赤行聞言也笑:“既然覺得無趣,那就不必再去了。”
龐斑斜靠在欄杆上,晃悠着手裏價值千金的琉璃燈,燈火映得他眸底光華明滅,心思莫測:“師父不幹脆殺光那些人嗎?雖然不能治本,也能治一時的風氣。”
蒙赤行道:“我只答應保護鐵木真的子孫安全,其餘事不該我插手,雖然很多人說,蒙元是在我的幫助下建立的,但我不是蒙元的皇帝。”
“何況,就像我曾對你說過的那樣,生與死本就是自然輪回的一部分,一棵樹、一朵花如此,一個人,一個家族,一個王朝自然也是如此。”
言下之意是只保護鐵木真子孫的生命安全,而全不管蒙元的長盛與否了。
龐斑就着倚靠的姿勢仰頭向後看,在他現在的視野中,明月沉在夜色裏,草木從天上向下伸展,庭院建築漂浮倒懸,人間的燈火如星辰,連蒙赤行都反綴在橫亘無垠的大地上。
整個世界都随着他的動作颠倒過來。
可若是從他在現代學到的知識來說,所有人腳下的大地都是一個球體,晝夜本就同時存在,只是身處地球不同區域的人能看到的景象不一,甚至世間沒有天地之分,地球只是鑲嵌在宇宙中不停旋轉的球體。
他們對地球另一邊的人來說,本就是倒挂着,現在的颠倒反而是一種歸正。
多麽神奇而有趣的世界。
龐斑漫無邊際地想着,在他鑽研道藏的十年裏,他斷斷續續恢複的記憶都是關于現代和東方不敗的,近來他更是從記憶裏開始接觸《天地交征陰陽大悲賦》,兩代魔教教主的經歷塑造了他的部分性格和行事風格,他也有意用這些魔念來打磨自己從浩瀚道藏中培養起的道心。
禁不起魔念拷問的道心當然不夠堅定。
道家的超脫和魔教的唯我兩種思想在他腦中拉扯,這讓他時不時會放飛自己的想法,體現在外就是會經常發呆,說些不着邊際的話,作出奇怪的舉動。
不過現在的魔念還沒有形成真正的魔種,所以這種拉扯尚不算嚴重。
蒙赤行沒有管他仰身向後的怪異姿勢,依舊在看他面前的樹。
龐斑忽然開口道:“我接下了國師的位置,鐵穆耳向忽必烈汗提出,想要為我建一座宮宇,被我拒絕了,我在這座府邸中長大,并不想去別的地方居住。”
蒙赤行道:“你這練法确實有意思,明明道心已現,偏偏魔念也重,你以精神為底力催動自身七情,助這一點魔念在道心清淨的道韻中凝練,情緒也比往日旺盛,否則以你的性格,并不會這麽輕易被引動殺機,還對這處宅邸産生眷戀之情才是。”
“等你的道心穩固,就要以執念凝聚魔種麽?我也很好奇,斑兒你會有怎樣的執念?”
只有所求不可得,或是天生偏執,才會形成執念,這執念要沖破穩固平和的道心,壓制洶湧起伏的七情,必定堅如磐石,千磨萬擊也不放松絲毫。
龐斑在最豐足的環境中長大,無論是物質還是精神上,他都很難有什麽絕難磨滅的“執念”。
但蒙赤行并不為此擔憂,他摸了摸弟子的頭:“十六歲,還年少得很,等你二十六歲、三十六歲、四十六歲,經歷過江湖事,見過各種各樣的人,自然會慢慢找到自己要追尋的東西。”
——————
從龐斑走出藏書庫起,蒙赤行開始将自己所會的魔門絕技一一傳授給他。
這實在是一個武學昌盛的世界,顧绛曾經身為東方不敗和公子羽時期所學的東西放到這個世界,很多都用不上了,蒙赤行教給他的東西正是他所需要的。
蒙赤行一脈的武功以鍛煉精神,從而幹涉外界物質為主,而要幹涉外界物質,首先從自身練起,從精神所發的頭部,衍伸到全身經脈,鍛煉筋骨,最終內外皆如水晶琉璃,頭部不再是命門,精神可以随意外放,甚至一眼就能看進別人心中,種下敗北的念頭,令對方不戰而降。
而這只是最簡單的一種用法,更多高深的法門堪稱神奇莫測、怪誕陸離。修行這種精神法門除了心性的要求外,“智能”二字也極為重要,正在于其人要有超出常人的智慧,能夠運使這種力量,不被常理的思想束縛。
修行到高深處,可奪天地造化。
“《藏密智能書》是魔門中專修精神力法的武功,魔門的絕學中大多涉及精神,配合本門的技法施用,正是因為魔門不尊禮教,唯任性情,只修自我精神,所以許多法門都損人利己,被正道視為邪道,也屬常事。”
魔門因為看重自我而放縱性情,蔑視法度和道德,這種放縱得出的真性者少,更多是放縱了自身惡念的人,走入另一個極端,這些極端大多體現在他們的行事上:雙修交合汲取對方的內力,殺人取血灌體,為了激發狂性肆意屠殺,為了收一個合心意的弟子就殺光孩子的全家,将其作為孤兒抱走等等,都是常事,更不要說一些格外殘忍的手段。
這也是顧绛覺得他們不入流的原因,任性自我不錯,可将自己完全迷失在外界感官中,把那種刺激中的高亢情緒視為“自我”,恰恰是沉淪入了外魔,被放縱的快意感染失去了真我,如果他們能從這種放縱中保持住一線清醒,最終斬去所有外相,或許能成,但除了蒙赤行,顧绛就沒見過魔門有達到這種境界的人。
“其實還有一個人,你應該聽說過,陰癸派的門主,曾經中原魔門的第一人,血手厲工。”蒙赤行對這個曾與自己争鋒的人物評價不低,“他年輕時也曾一度嗜殺成性,所以招惹到了令東來,沒有人知道兩人之間發生了什麽,但從那以後,厲工就上天入地地尋找令東來,再也不複昔年行事。”
“令東來。”顧绛緩緩念着這個名字,“世人都說,無上宗師令東來是當時的天下第一人,師父見過他嗎?”
蒙赤行緩緩搖頭:“在為師看來,令東來是個不世出的絕頂人物,他并非出身名門,只靠自己學劍,三十歲便進天人之境,縱橫天下無一敵手,可他的行蹤極其缥缈,據說他曾來過北方,可那時我還在藏地潛修,而且那時我的境界遠遠不及他,就是現在,我也不敢說自己的修為就趕上這位無上宗師了。”
“厲工我倒是很熟悉,他這個人秉性極傲,他苦尋令東來多年,絕不會是因為敗在他手中的緣故,若只是技不如人,他多半會潛心苦修,一日不能贏回這一仗,一日不見對方,就像他當年在我手中落敗後一樣。”
蒙赤行和厲工雖都是魔門出身,但魔門內的争鬥有時比外界更狠厲,他們之間的摩擦不少,這也是蒙赤行收攏天命教的緣故,意在分裂陰癸派,但争鬥歸争鬥,個人歸個人,厲工是蒙赤行在魔門中少數幾個看得上的人物之一。
“可他一心尋找令東來,那只能說明,他在令東來身上看見了自己渴求的東西。”
說到這裏,蒙赤行悠悠一嘆:“當初我有所猜測,卻不是真的明白,但是在和傳鷹交手後,我明白了。”
顧绛笑道:“看來,這個曾與師父為敵的傳鷹,也是師父心中唯一的對手和朋友。”
蒙赤行慨然而笑:“說得好。道途艱難,尤其是我魔門修行先易後難,比起道門入道的先難後易,水到渠成,魔道之人想要走出最後一步更是千難萬險,這個時候能有一人同行,無論彼此的立場如何,都是一樁值得歡喜的幸事。”
“為師能與他長街一戰,跳出魔道,轉向天道,實乃大幸!”
——————
在顧绛用精神力影響一只栖息在後院樹上的小鳥,逗它和自己閃躲騰挪,往來嬉戲的時候,忽然皇宮的方向傳來鐘聲。
哈日珠匆匆奔到後院,跪拜在地,對蒙赤行禀報:“主人,薛禪汗駕崩了!”
随着消息傳開,陣陣悲聲呼嘯響徹大都,如群狼哀嚎,是那些追随忽必烈征戰天下的蒙元高手,得知魔皇去世,放聲悲號,呼喊聲伴着鐘聲久久不息。
一時間,大都中滿是被嚎聲中的凄怆哀厲之意感染而發的哭聲。
顧绛坐在樹上,那毛絨絨的藍白色鳥雀停在他手背上,還在用翅膀拍着他的手,催促他繼續,顧绛摸了摸它的頭,抽離出自己的精神,将它放飛。
樹下蒙赤行背手望着皇宮的方向,看了許久,哈日珠和顧绛都未開口說話,直到鐘聲平息,他才用平靜的聲音說道:“我已知曉了,該怎麽置辦,你看着辦就是。”
“雖然早有預料,但他今日走得突然,斑兒,跟為師去送你師兄最後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