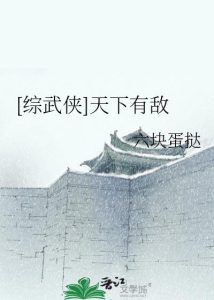道魔 4
四日前,龐斑還見過忽必烈,那時的他談笑自如,舉止豪邁,衆多魔門高手為他當場宰殺牛羊,種種手段齊出,就為了恭維讨好這位坐擁天下的魔皇。
如今,忽必烈躺在龍床上,雙眼緊閉,神态平和,已經斷了生息,随着他的魔功停止運轉,屍身也漸漸老化,精氣流逝後的軀體終于有了八十歲老人的幹枯,黑發變得蒼白枯朽,瑩白的皮膚包裹着血氣不再旺盛的骨肉,顯得松弛。
仿佛這具身軀內的靈魂已經離去,只留下皮囊像一個口袋,裝着殘留下的部分,卻裝不滿。
在龐斑又陷入奇思怪想中時,蒙赤行已經問過了忽必烈去世前後的狀況,讓鐵穆耳出面穩定朝局,并按照過往汗王去世的習慣,為忽必烈潔淨身體,換上喪服,按照蒙古人的習慣,他們生前享受富貴榮華,死後卻葬得儉薄,不必特意去制作壽衣,只要找到他生前最喜歡的一套衣服,并他的武器、用具,就可以入棺下葬了。
在一衆哀哭不已的文武官員、宮妃內侍中,蒙赤行師徒二人的平淡顯得這樣突出。
但絕沒有人敢對此說什麽,蒙赤行作為帝師,已經經歷了許多成吉思汗子孫的死亡,甚至是成吉思汗自己在六盤山過世時,也是蒙赤行砍倒古樹,将樹幹劈成兩半,為成吉思汗收斂屍身。
今日也不例外。
早在得知自己死期将近時,忽必烈就命人取了足以制成棺木的楠木來,剝去樹皮,曬幹打磨。
蒙赤行将這段楠木劈開,鑿出足以容納屍身的空間,親手将忽必烈的屍身用白布包裹後,放入樹棺中,龐斑跟在他身後,手裏捧着忽必烈生前所用的大弓和刀劍,等屍身放置好,便随之一起入棺。
忽必烈手下的四位大将負責将他的棺木送到殿中,準備等待諸位皇親國戚、王公大臣叩拜,最後會由蒙赤行用金箍封棺,進行密葬。
龐斑看着他們一步步将忽必烈安置好擡走,若有所思地打量着殿中的人,他們都在哭,但被精神催動的魔念能夠感知到他們悲傷外表下的真實情緒。
有的人面上的在哭,心裏在笑,覺得魔皇離去,鐵穆耳是個保守到有些懦弱的人,最好拿捏,他們等不及想要在搬離這座大山後操控風雲了;有的人是真心在哭,卻不是為忽必烈,而是為自己,他們害怕自己會被要求為薛禪汗殉葬;還有些人不高興,也不難過,只是所有人都在哭,自己也該哭泣罷了,最好哭得傷心些,莫要教人挑出來,吃責罰。
當然,也是有不少人确實在為自己的君主傷心欲絕,忽必烈的去世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時代的落幕。江山已定,天下已分,他們再也不能跟随忽必烈策馬揚鞭,征戰天下了。
長風悠悠,蒼穹無垠,放馬陰山,哀哉何極?
而坐在忽必烈的棺邊,欲哭無淚的女子正是忽必烈的第二任皇後南必,這位拜入天命教下的繼任皇後,在忽必烈心灰意懶不見人的時候,一直掌握着朝權,她看起來年輕又美麗,身上魔門秘法修行得也不錯。
她本以為等忽必烈死後,自己還可以繼續掌權,即便闊闊真和鐵穆耳容不下她,她頂多詐死脫身,回到天命教去,可剛剛蒙赤行開口,指名要她為忽必烈殉葬:
“南必,你是忽必烈的妻子,他這些年都靠你照顧,他今日離去得突然,你跟着去照顧好他。”
言罷,堂下的哭聲都愣怔了片刻,但沒有人質疑蒙赤行的意思,哭聲又繼續在殿中回響,似乎蒙赤行只是要了一碗水,而不是讓皇後殉葬。
蒙赤行已經久不管政事了,突然開口,這顯然是忽必烈生前就已經瞞着南必,和蒙赤行交代過。
十二載尊榮,多少恩愛前事,忽必烈連權力都願意和她共享,她還以為汗王是真的迷戀愛護她,卻原來魔皇從未真正憐惜過這個枕邊人。
南必沉默着,她知道自己逃不掉的,蒙赤行就在這裏,忽必烈已經用萬全的辦法斬斷了她的退路和生機,何況她還有一個兒子。
龐斑見她沒有異動,便看向了在場唯一一個蠢蠢欲動的人——忽必烈的長孫、真金的長子甘麻剌。
作為察必皇後撫養長大的孩子,忽必烈曾十分寵愛這個孩子,甚至做好了讓他繼位的準備,但忽必烈晚年還是為兩件事猶豫了。
第一是蒙古的傳統,講究幼子繼承,長子繼承制是漢人的傳統,他若讓甘麻剌繼位,是不是在皇位繼承制上也從了漢風。
第二,甘麻剌本人更親近正道一脈,對魔門的許多行徑頗有微詞,魔門之人恐怕不會支持甘麻剌。
事實也的确如此。
在《笑傲江湖》的世界,門派勢力如何做大,也只能在野行動,影響不到朝廷的運行,而公子羽哪怕掌握天下財運,也是要和官府打好關系的。
可在這個世界,皇朝權力的更替背後都是正魔兩派的争鬥,實在是個人武力之間的差距被拉到天壤之別,不再是武林魁首為國家服務,而是國家供養大宗師來維護國家安全。
隋末時炀帝攻高句麗,就是奕劍大師傅采林率衆守住了高句麗,在兩國國力差距如此之大的前提下,可見這位奕劍大師的本事。
而蒙元朝廷中,之所以魔漲道消,正道被魔門打壓,并不是因為忽必烈出身魔門,而是因為蒙赤行的存在,他只要願意為魔門出頭一天,正道只要沒有人能勝過蒙赤行一天,正道想要奪回話語權就是不可能的。
高句麗人視傅采林為神,突厥人視畢玄為神,蒙古人視蒙赤行為神,是因為他們與普通人之間的差距,的确猶如神人。
所以蒙赤行站在忽必烈的棺前,底下人無論心思如何,都只能低頭跪拜哭泣,心思蠢動的人甚至不敢擡頭看向他,而他說出口的話,就是定局,哪怕曾經弄權的南必皇後,他要她殉葬而死,也沒有一個人違逆。
以一人之力橫壓天下,不過如此。
——————
忽必烈在一個晴天被擡出皇宮秘密下葬,鐵穆耳成為了蒙元新的皇帝。
和忽必烈同葬的除了他生前慣用的器具,他喜歡的馬匹和獵犬,還有他寵愛的皇後。
南必沒有掙紮,她穿着自己最喜歡的衣裙,梳起長發,用珠寶點綴自己的衣衫發冠,行走在送葬的隊伍中,用蒙語唱着歌,一路來到相看好的葬地。
看着伯顏等人将棺木放入地下後,南必也跳下了墓中,任由他們将墓室封填,恢複成平地的模樣。
蒙古人認為,只要沒有厚葬,沒有墓碑,後世就不會有人盜掘皇陵,驚擾地下的亡靈。
哪怕建立起這片土地的封建王朝中領土最廣袤的王朝,他身後所能占據的不過是地下一個墓室。
龐斑坐在封土前,用陶笛吹奏起南必吟唱的歌謠,送葬的幾位蒙人将領伏跪在地,久久不願起身。
回程的路上,蒙赤行對龐斑道:“這樣的事,你以後的歲月裏還要經歷許多,似咱們這樣的武道修行者年歲漫長,在這個過程中你要送別很多人,今日是師兄,明日可能就是師父,未來還有更多的人。”
龐斑笑道:“我明白的師父,即便有前人、後人、同行者,這條路依舊只能一個人走下去,我也早就習慣了寂寞。”
蒙赤行嘆息着拍了拍他的肩,先他一步向前而去。
——————
忽必烈死後,蒙赤行除了教導龐斑,其餘時間都進入閉關的狀态,這樣的狀态持續了整整十年。
這十年裏,龐斑代替他守護大都皇宮的安全,和深居簡出的蒙赤行不一樣,龐斑的情緒時有起伏。他高興時,正道人士殺了魔門的人從他面前路過,他還能為他們指一指離開的路,他不高興時,徑直到宮中把不安分的人屠戮一空也是常事。
鐵穆耳和太後闊闊真都頗為畏懼這位少年成名的“魔師”,主要就是因為他的喜怒無常。
恰恰因為他的情緒難以捉摸,兩派之人反倒不怎麽敢在大都鬧事了,誰也說不準,這位會不會突然走進來,把他們全殺了了事。
他們也想過要不要集中力量拿下這位魔功還未大成的蒙古國師,但想到他身後的蒙赤行只是閉關,不是真死了,若是弟子出事,把蒙赤行招惹來,恐怕不僅不能如願,還要折更多的人手進去,便作罷了。
反正對魔道之人來說,死的只要不是自己,問題都不大,就當魔師動手為他們騰出位置來了。
這十年間,龐斑的面相又有了一些改變,他的面部輪廓棱角變得柔和,像是公子羽,五官正中的鼻子挺拔秀氣,像是齊乘雲,這使得他青年時的樣貌比起少年時的淩厲,變得溫和不少,甚至顯出了三分女相。
随着《天龍》世界的記憶恢複,齊乘雲時磨砺而成的道心已成,這也激發得他的魔念張揚,穩固的道心對無根的魔念挑釁無動于衷,所以看起來龐斑行事任性,殺人立威魔性十足,可細細琢磨他行事的準則,卻都是為穩固大局出發的,以至于蒙赤行長期閉關不出,大都中也沒有發生當初真金太子的慘案。
明明鐵穆耳的能力和威望遠不如忽必烈,蒙元這十年的朝局卻清明不少,鐵穆耳做到了一個守成之君該做的事,試圖與他争奪皇位的晉王也安安分分地呆在自己的屬地。
在魔門的統治下,經營出一派黃老的太平氣象,可見他心中還是道心為主。
那輪彎彎的明月又挂在了他的心境中,可月亮要皎潔清明,不僅要自身明澈,還要夜色足夠深沉,他現在心境中的夜色如煙霧般起伏,時常被月色浸透。
龐斑撐着頭側卧在後院長石椅上,天寒地凍的時節,哈日珠上了年紀之後裹着皮襖都忍不住發抖,他卻只着單衣敞着外袍,渾不在意。
細雪未止,落了石椅上的人一身,他兀自阖目神游,吐出白氣如煙,在風中都不飄散,又被他緩緩吸入肺腑中,一只藍白色的鳥雀窩在他袖中,已不知繁衍多少代的鳥兒團成一團入睡了,他卻似睡非睡。
蒙赤行走過來的時候,正看到他指尖微動,将空中細雪凝做紛紛白蝶,上下翻飛,還有幾只落在一叢山茶花前,流連不去,似活物一般,或者說,寄存了他一點精神的冰蝶本就是“活”的。
捉起一只打量,只見蝶翅晶瑩剔透,上面的花紋脈絡分明,連蝴蝶的觸角都輕顫着,一點都不畏懼蒙赤行,就落在他食指上停歇。
蒙赤行輕輕地将它放在自己肩上,走到神游八表的弟子身邊,龐斑懶洋洋地坐起身,望向面帶笑意的蒙赤行。
他像每一個疼愛晚輩的師長一樣,伸手撣了撣弟子身上的積雪,才在龐斑身邊坐下,開口道:“斑兒,百日後,為師的死期就到了,到時候我會坐化而亡。”
“到時候,為師的屍身你不必遵循風俗入葬,用烈火焚燒,化為灰燼,散入天地即可。”
說這話時,蒙赤行是笑着的,他的心境沉浸在一種莫大的歡愉滿足中,龐斑甚至能感覺到他一向約束極好的精神在外放,可這精神半點沒有昔日冰冷殘酷的魔意,反而柔和浩蕩,幾乎與天地融為一體。
這是精神修行已經圓滿的表現。
百日之後,他的精神就會脫出□□,融入天地。
龐斑忽怔怔落淚,而後歡喜地笑道:“恭喜您,大道成矣!”
蒙赤行慈祥地微笑着像他年幼時那樣,摸了摸他的頭:“我要感謝你,若不是你為為師耗費這十年,我還沒有這麽快就功成圓滿。”
龐斑道:“所謂師徒,我在懵懂時,您引我歸入道途,您在關隘時,我為您了卻後顧之憂,本就該如此。”
說完,他問道:“您要回草原去嗎?”
龐斑還記得當年蒙赤行說起故鄉的神色,只是那時他還有許多放不下的事,如今都可以放下了。
果然,提起歸鄉,蒙赤行恍惚後,喜不自勝,他望向北方道:“是啊,是啊,我該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