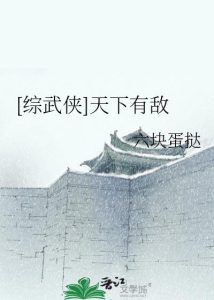道魔 9
顧绛有一瞬間不确定對方是在叫自己。
直到那茶棚老板轉過身,眼神怪異地看着他,他才确定那人确實是叫自己“邋遢道人”。
随之就聽到另一人呵止道:“小山,怎可對修行人随口呼喝無禮?去向那位道長致歉。”
那年輕人不耐煩地反駁道:“就是知道你禮敬道家,我才喚他過來的,你見到那些道人不都要表現一番的嗎?這會兒又嫌我不敬。”
顧绛轉過身看向起了争執的兩人,這一桌有三人,兩男一女,起了争執的兩個男子樣貌相似,多半是父子,其中年長的約四十來歲,做文士打扮,年少的一身武服,有些拳腳,還有一個七八歲小姑娘眨巴着眼睛看着兩人,沒有插嘴說話。
那姑娘見顧绛轉過身來,睜大了眼睛,小聲驚呼,扯着中年人的袖子:“爹,爹,神仙。”
背對着顧绛而坐的文士和“小山”暫停了争執,齊齊順勢看過來,年輕男子在顧绛的視線中不吭聲了,倒是那文士站起了身,行了一個道家的禮道:“這位道長,小兒無狀,冒犯您了。”
顧绛不至于和一個反感自己父親求道的孩子計較,便回了一個禮,開口道:“無妨。”
楊遠看着眼前人,心中驚嘆,雖然衣着褴褛,可此人實在好相貌,面如冠玉,俊美非常,雖然眉眼秀麗到有些女相,卻沒有那種五官過于精致帶來的攻擊性,相反,他的氣質平和淡泊,頂多有些修道人常見的清冷,如冰如玉,有昔年看殺衛玠的風采。
這年輕道士破損的衣物,配合着這張臉,楊遠都要懷疑他是不是游走修行時被哪個女大王給劫了,一番争鬥後逃出生天,才搞得如此狼狽。
這南方重山中可有不少山寨,不服蒙古人,自成一方勢力呢。
楊遠這念頭才起,那挽着道髻的男子就看了他一眼,陽光下,那道人烏丸似的眼珠旁好像還有一圈淺光,清淩淩直看到人心裏去,惹得他不由自主打了一個激靈,但他本就好黃老之說,見狀反而越發熱絡了,請引對方入座道:“道長,風塵仆仆,何不暫歇一歇腳,飲一杯茶水再走呢?”
顧绛想了想,沒有推辭,邁步走了過去,之前大聲招呼他的年輕人自覺地站起來,抱着妹妹坐到下首位置去。
見顧绛打量他,剛剛還滿腹怨氣的少年默默垂首,恨不得把臉埋進茶碗裏去。
楊遠知道自家兒子抹不開臉,便笑着替他解圍道:“在下姓楊,單名一個遠字,這是犬子軌山,小女安安,我父子三人偶然從此過,沒想到能遇見道長這樣的人物,敢問道長道號,在何處入道?”
顧绛悠悠道:“貧道于終南山下入道,號容忍。”
楊遠一時語塞,倒是那小姑娘咯咯笑了起來,楊軌山臊不過,起身倒了一杯茶放到“容忍道長”面前,道:“是我不修口德,冒犯了先生。”
顧绛端起茶抿了一口,楊軌山見他接了自己的茶,便是不計較的意思,松了口氣坐下。
明明此人看起來比自己也大不了幾歲,可楊軌山就是心裏怵得很,便是武館裏的館主威風八面,他見了也沒有這樣緊張心虛。
顧绛道:“楊居士家學淵源,小公子自幼耳濡目染,有幾分慧根。”
楊遠聞言也笑道:“是,我曾見過武當山的盧道長,他也誇這孩子有些道緣,但我自己都為家室所牽挂,不能全心向道,何必為難這孩子呢?”
顧绛聽他提到武當山,忽然想起一人,是啊,以眼下元朝時節,武當山應當有一位足以開山立宗的道家高人,自己心有疑惑,可以去找他論道,便詢問道:“楊居士認得武當山的道長,可曾見過三豐真人?”
在道門,能被叫一聲“真人”的都是有道高人,可那楊遠并楊軌山都面露迷茫之色:“三豐真人?武當山上道觀衆多,那裏的道士我當然見不全,但能被稱為‘真人’的道長中,并沒有道號‘三豐’的。”
楊家父子滿心疑惑,顧绛比他們還茫然兩分,他本以為蒙赤行去後,天下第一的高手就該是那位“得天地之造化”的真人了,可這個世界竟沒有此人嗎:“武當山沒有三豐真人,那道門如今的‘道尊’是誰?”
蒙赤行的魔門勢力畢竟是從草原進入中原的,這一脈本是初唐時魔相宗和滅情道結合、于突厥部落一直流傳下來的,和中原陰癸派一脈是死敵,一直被陰癸派攔在關外,所以在蒙元奪得宋國前,他們對中原門派的事情了解不深,等蒙赤行轉入天道,他們師徒倆又都是不問事的性子,知道的更少了。
顧绛上一次詢問道門的情況,還是年少時聽聞了慈航靜齋和淨念禪院的正道聖地名聲,他才好奇佛門聲望如此大,道門是如何與其相抗的,蒙赤行告訴他,道門一直有太清宮道尊坐鎮,雖不争這名頭,勢力也不容小觑,北宋末年那位幾乎将佛門化入道門的林道士,就是那時的道門道尊。
和門下弟子大多在山中的慈航靜齋不同,道門的人越是亂世,越喜歡下山證道,元滅宋的過程中,他們的弟子損傷極大,不複昔年壓倒佛門的氣焰,人也少出來走動了。
再怎麽清修,穩固人心的道門尊者應該還是極為有名的,普通信道之人也該知道如今道門之首的名聲才是,否則怎麽能鞏固道門勢力?
但這一次楊遠幹脆搖了搖頭,反問道:“道門那麽多支脈,各家法脈不一,誰都不服誰,居然還有道尊的麽?還是說,這是龍虎山當代天師的另一種稱呼?”
顧绛知道是問不出什麽了,轉而提起了自己最初的問題:“不知如今是哪一年,哪一月。”
山中清修的道士忘卻年歲倒也正常,楊遠答複後,顧绛才豁然發現自己竟在驚雁宮中呆了五年,三年前鐵穆耳就去世了,如今的蒙元皇帝是他的侄兒海山。
新的蒙元皇帝篤信密教,佛門還好,道門已有沒落之态,再不複當年忽必烈平衡各派的情勢。
楊遠本也是科舉考中的官員,只因吏治敗壞、世道渾噩,做官就是幫蒙人壓迫底層漢民,他不願如此,才棄官而走,轉為尋仙向道。
可妻子怪他悲憫別人卻不為家中着想,雖不愁生計,但有人做官和平民百姓家截然不同,夫妻倆争執後,妻子氣得生了病,楊軌山聽說母親病倒趕回來,見母親病中模樣,便和父親拗起了氣。
哪怕不提母親的病,楊軌山也極不贊成父親辭官向道的行為:“你也知道如今好官少,狗官多,那你一走,豈不是又少了一個,你不去為民做主,反倒去修道,整日和道士往來,難道還能把天下修好不成?”
楊遠苦笑不已,少年人心清氣正,天不怕,地不怕,哪裏知道在如今的官場中要保住良心,可比辭官難得多。
顧绛聽罷,不再詢問,喝完杯中茶後,便告辭離開。
——————
按照原有的計劃,龐斑一路回到大都,發現蒙赤行的府邸外有不少探子,顯然是他們師徒一去五年,不知蹤跡,很多人的心思都活動了。
龐斑也不叫門,自行推門入戶,正在堂前打掃的仆人一擡頭,見是穿着一身道袍的少主人,連忙驚呼道:“小主人!您回來了!”
他這一聲,驚動了府上的其他仆從,七人匆匆趕到堂前,站在最前面的哈日珠喜不自勝,她是照顧小主人長大的,情分非旁人能比,在諸仆從單膝跪下行禮時,只有哈日珠撲上前握住了龐斑的手:“小主人,您可回來了!”
這些年,他們這些蒙赤行的下屬都猜到主人是成道而走了,可蒙赤行走了,他們就該跟在龐斑身邊繼續經營魔門勢力才是,結果小主人也跟着主人一起不見蹤跡,好不容易發現了去向,又行色匆匆不願回來,然後消失在了南方,了無音訊,一去就是五年。
魔門中不少人都覺得蒙赤行的徒弟,這位年少的蒙古國師已經死了,極有可能是正道之人暗中下手圍殺了還未魔功大成的龐斑,防止他成長為第二個蒙赤行。
鐵穆耳死後,海山甚至另封了一位藏地喇嘛做國師。
龐斑任由哈日珠給他解開道髻,另外梳頭戴冠,一邊聽着她敘說如今大都的形勢,聽說新國師是個喇嘛,問道:“應當不是鷹緣活佛吧。”
哈日珠見到龐斑回轉,放下了心底的大石,神色輕松地回複說:“當然不是藏地活佛,那位在藏地的地位極高,但是很少出布達拉宮,一心潛修佛法,咱們如今這位皇帝倒是想請他,都被推拒了。”
龐斑也覺得鷹緣那性子,不會樂意到大都來做這勞什子的國師:“那這位國師的修為如何?”
哈日珠啐了一聲:“哪有什麽修為,都是天命教一路的人,整日和皇帝在宮中嬉鬧,荒淫無度,搞得大都烏煙瘴氣。”
龐斑看了一眼鏡中哈日珠生了皺紋的臉,道:“既然國師的位置已經有人負責了,大都又烏煙瘴氣的,那就走吧。”
哈日珠愣了一下,才問道:“少主要離開大都,去往何處?”
龐斑道:“哈日珠,你一生都在為師父和我操心,如今師父大道已證,我也只差那一步了,我打算游走天下尋找突破的機緣,你也可以為自己想一想,沒有師父和我,你想過什麽樣的生活。”
青年男子微微側身看向她,輕描淡寫道:“你是想要繼續住在這裏,還是回自己的故鄉部落去,亦或者你喜歡大都這個權利中心,我也可以去殺了海山和那群喇嘛,屆時,你再扶一個合心意的繼任者。”
哈日珠承認自己剛才是有心向少主告狀,畢竟蒙赤行不在的五年,他們這些帝師的舊部雖然依舊被蒙人尊崇,可魔門的人沒少上門惹事。見蒙赤行師徒長久不歸,打起府中藏書主意的人都有,就是蒙赤行的下屬,忠于他,卻未必願意繼續跟随龐斑,五年裏散去不少。
她知道,這裏面多半是陰癸派推動的,但沒有蒙赤行坐鎮,他們的确敵不過陰癸派如今的主事者。
“唔?”龐斑終于有了點興致,“是誰?”
哈日珠擦了擦有點冒汗的掌心,繼續為龐斑戴上發簪:“是厲工和符瑤紅的師弟,邪佛锺仲游,他手下有陰癸派和天命教兩方的勢力,號稱如今魔門第一高手。”
龐斑笑了起來,他原本淡漠出塵的氣質,此刻流露出懾人的魔性來,魔種吸引着所有人的心靈,卻又彰顯自身的冰冷無情,放在龐斑身上,還有些許戲谑:“他既然如此稱號,便是自覺能與師父比肩了,沒想到師父一走,魔門中就有這等人才出現,我若不請教一番,豈不遺憾?”
哈日珠已經習慣和魔門的絕頂高手相處,一覺不對就低下了頭,放空心思,以免被對方外放的氣勢所傷,但這一次她沒有感覺到冰冷的精神,反而心跳本能加速起來,感覺自己平穩的情緒翻騰,多年來對蒙赤行的仰慕,因他離去而生的悲傷,再一次見到龐斑的歡喜,以及這五年來對權勢的渴望,都難以遏制地沖破了心防,使得她幾乎難以自控地落淚。
龐斑凝視着哈日珠,曾經她跟在蒙赤行身邊,蒙赤行的存在就給了她高于所有人的地位和權力,現在蒙赤行離去了,她想要自己掌握這權勢。
可以,為什麽不可以?
魔本就是最任性自我的存在,從不會鄙夷正道排斥的野心、名利、權欲,對魔而言,這些本就該圍繞自己而生。
龐斑伸手為她擦去眼角的淚,也拂過她眼底熾烈的光:“我自幼便是你照顧,你對師父最為赤誠,所以師父也放心你,無論寒暑,你都悉心呵護,從不假手于人。”
“我總得回報你一些什麽,才能放心離去。”
“這三條路中,你有心選最危險的一條,我不會留下保護你,但我可以替你掃出一條路來,能不能把握住機會,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