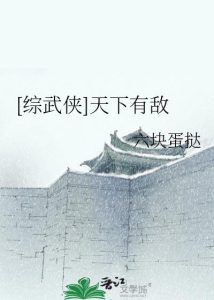迷天 40(完)
人發殺機,天地翻覆。
仿佛神話中大羿開弓、射落九日的傳說,以人力撼動天象。
在人目力不能及的重重烏雲後,血紅的劍氣與被鎖定的異物碰撞在一起,尖銳的聲響如同金烏隕落前的哀鳴,響徹天宇。
什麽樣的力量才能在逆空直上後,還能摧毀那震鳴不已的異物?
沒有人直面這一箭,只見關七身邊所有的建築如狂風中的枯草倒塌,就可窺見一隅,更不要說那些射向他的箭雨和劍氣,根本沒有傷到他,就在這一箭的餘波中消弭了。
反應稍慢的人都留在了神通侯府的廢墟中,僥幸逃離的人劫後餘生,止不住地喘氣平緩心跳。
雷媚擡頭看着已經空出一片的雲層,那躲在雲層後的東西不見了,只有血河劍留下的劍痕殘留在夜空中,還未散去,透過箭矢破開的空隙,有光亮灑落下來,照在始終立于原地的關七身上。
射出這樣的一箭後,哪怕是關七,都該力竭了。
這些被勒令來圍殺他的人卻沒有一個敢上前。
雷媚自诩是個膽大包天的人,所以她敢操控人心,在各種勢力中來回橫跳,可看着依舊擡頭望着天的關七,她第一次感到了“恐懼”。
當一個人所擁有的力量已經超出了你的理解,你知道對方殺死自己和碾死一只螞蟻沒有什麽區別時,你當然會對這種無法理解、無法揣測、無法企及的存在感到恐懼。
尤其是剛才她出了一劍。
現在回想起來,雷媚居然有點想笑,笑自己也有這種“蚍蜉撼樹”的勇氣。
剛剛那一劍是她能抓到的最好的機會,雷媚一直知道金鳳細雨樓是她的對手,但不是她最大的威脅,蘇夢枕這個人并不喜歡趕盡殺絕,他的目的一直是團結手裏的力量去做一些保家衛國的事,一些需要很多人才能做成的事,這注定了他會珍惜人力。
可關七不一樣,他自己就已足夠震懾天下。
在雷媚年幼時,她就知道迷天盟這個六分半堂最大的敵人是怎樣的幫派,它就是圍繞關木旦建立起來的組織,失去關七,就是一盤散沙,但關七恰恰也是迷天盟最不可撼動的存在。
這樣的關七必然是自傲且極有野心的,像獨自盤踞一山的老虎,擠壓着其他猛獸的生存空間。
所以她和雷損往來,因為雷損一步步将關七陷入了險境中,在雷媚看來,這個男人确實比自己的父親強,這種強不在武力,或者說不止在武力,還在心性手段上,而她爹有些時候太過直硬了,連唐見青都哄不好,愣是讓這位唐門的高手斷情離去,若是唐見青願意嫁給他,結合唐門的部分權勢,雷媚也不會想着聯合雷損。
畢竟雷震雷是她的親生父親。
雷媚看着關七,很難不想起雷震雷,那個在被奪走權勢後終日沉默的男人,最後還是作為父親為她開辟了一條生路。
她這一生交往的男人有不少,從最初的雷損,到剛剛喪命的方應看,他們都是為了權力和她彼此利用,或許那些算計裏,偶爾也會有一絲溫情,但雷媚自己也不甚在意,她深知這些男人的秉性,和他們談感情是沒有用的。
雷損說是喜歡溫小白,可利用起溫小白來刺激關七、利用溫小白的女兒挾制關七,順手得很,還有方應看,他心裏念着的那個人好像是他心裏最溫柔神聖的存在,可他決心刺激方歌吟、算計桑小娥時,也沒有半點手軟。
男人可以無情無義,女人為什麽不可以?
要不是關七下手太果斷,雷媚絲毫不介意在局勢調轉時,反手紮這些曾同床共枕的人一刀。
可惜了,這世上除了雷損、方應看這樣的人,還有蘇夢枕、狄飛驚這樣的人——要是現在雷媚還反應不過來狄飛驚的立場,她就是被這人坑死也活該了。
還有關木旦。
這樣的人存在,讓所有陰謀算計都顯得可笑起來,雷損和方應看步步為營,窮盡心思對付他,卻被一力破萬法,枉誇聰明。
啊,現在大概還有她自己也算在其中。
雷媚忽然有些想念雷震雷,這個世上唯一真心愛她的男人,可惜這一次不能再保護她逃出生天了。
他已經永遠地留在了一手創立起的六分半堂,而她今日死在這裏,六分半堂就會徹底掩埋在黃土裏,這個曾六分江湖的龐然大物,也和當初的權力幫、長空幫一樣,随着主宰者的逝去而覆滅。
想到這裏,被關七那一招“傷心小箭”的餘韻所動,她竟也悲從中來,默默落下一滴淚。
不知是為曾經煊赫的權勢坍塌,還是為了雷震雷和走到末路的自己。
——————
在确定天上的異象真的消失了之後,顧绛才收回視線,用出那全力一擊之後,他确實有些疲憊了。
體內的內力所剩不到一成,常年征戰的暗傷隐隐有發作的跡象,持劍的右手幾乎不能動了,那股傷人自傷的“傷心”之意幾乎震斷了他的小周天循環,使他無法勾連天地,利用自然之力療傷。
多少年,他都沒有這麽狼狽過了。
但即便如此,他也沒有馬上退走找個安靜的地方養傷,反而揚聲道:“趙佶就讓你們來殺我,未免太小看關某了,還有人嗎?”
“大內的高手難道無人了?”
站在廢墟中的男人衣衫褴褛,發冠也不知哪裏去了,披散着頭發,面色慘白,誰都看得出來他身受重傷,應該到了強弩之末。
可關七要殺他們,也用不了多少力氣。
似乎為了應證這一點,關七擡手發出一道劍氣,沿着雷媚先前偷襲的方向折返過去,雷媚拔劍應對,卻發現這道看似輕飄飄的一縷劍氣竟鋒利到了極致,穿透她的長劍後,直接沒入咽喉。
雷媚甚至沒反應過來,看着劍身上的孔洞,想要開口贊嘆關七用劍的出神入化,卻發不出聲音,這才明白自己的處境,伸手欲捂被劍氣洞穿的咽喉,轉念想想也無必要了,幹脆轉身尋到一處還算幹淨的斷壁,坐了下去。
這一坐下,就沒能再起身。
見此情形,領頭的守軍将領再次擦了擦額上的冷汗,命副官看守在此,自己匆匆離開。
——————
顧绛坐在還剩一半腦袋的石獅子身上,緩緩理順體內的小周天,似乎打定了主意要歇一歇,看徽宗能拿他怎麽辦。
帶着一部分禁軍趕到的諸葛正我看着他,心中感慨萬千,又有些好笑,這位曠世高手、多年老友胸懷豁達,但有時候的确有點促狹氣,喜歡擠兌為難人。
諸葛正我排衆上前,遙遙拱手道:“關兄,你今夜已經大鬧了一場,官家在宮中聽說了這兒的情形,他并不想和你為難,只想送關兄離開汴京城。”
在癡迷道學的徽宗眼裏,關七那一箭已經可以說是人間修行有成的“神人”了,他身邊那些國師、道長哪一個也沒有這種本事,他現在是真的不想和關七起沖突,反正關七手下的人也都是和金人過不去,沒有攻打過宋土,留着關七在,還能讓金人有所顧忌。
趙佶飛快地給自己找好了理由,轉身就想叫米有橋去叮囑諸葛正我不要得罪他。
結果一轉身,發現身邊的內監不是熟悉的老人,這才恍惚想起,米有橋去了神通侯府,被關七殺了。
趙佶嘆氣道:“米有橋是有忠心的,也聰明伶俐,就是年紀大了,比年輕時更重感情,放不下和他交好的神通侯。”
“都是命數,罷了,你去也一樣,給諸葛正我遞個話,讓他把握分寸。”
“是。”跟在趙佶身邊的太監彎着腰,恭敬地應了,誰也看不清他低垂的臉上是什麽表情。
反正諸葛正我見到他的時候,這位馬上就要頂替米有橋上位的公公笑得十分親和:“這是官家的意思。”
諸葛正我當然明白趙佶是什麽意思,也充分把他的想法傳達給關七了。
關七吐出一口氣來,有點有氣無力地道:“這天色,馬上就要下雨了,我千裏迢迢來此,趙官家卻要趕我淋雨離開,諸葛兄你看,我這一身狼狽,還把方兄的血河劍給毀了,連把傘都沒有,更不要說返回雲州的路費了。”
諸葛正我沉默了片刻,揮手讓人去取傘和銀兩來。
然而,還沒等取東西的人返回,一個小侍從就跌跌撞撞跑了進來,他直奔前來傳令的公公和諸葛正我,尖銳的聲音在極度緊張下,越發刺耳:“公公!公公!官家遇刺了!”
諸葛正我霍然轉身,目露精光,肅然喝問道:“怎麽回事?!”
他一開口,那小侍從哆嗦了一下,冷靜了不少,被傳令內監死死抓着手臂,咽了一口口水,顫巍巍道:“公公您離宮不久,就有賊人入宮來行刺,誰也不知道他是什麽時候、怎麽進來的,就聽到他說,他說——”
傳令內監追問:“說什麽?你快說!”
小侍從本來還有些猶豫,被一追問,不再顧忌,噼裏啪啦道:“那人說官家,官家殺兄弑母,迫走胞弟,殘害忠良,是,是篡位逆賊,他承先帝和向太後的遺願,有先太子遺诏在手,要殺逆賊以重振朝綱。”
言罷,小侍從雙腿一軟跪在了地上,傳令內監也仿佛五雷轟頂,反倒是諸葛正我馬上意識到了刺客的身份,他澀聲問道:“那人,是不是,刺客長孫飛虹?”
未等小侍從開口,他便縱身向皇宮趕去。
禁軍本就是守衛皇宮大內的,眼下宮中生變,他們也跟着諸葛正我匆匆離去。
人來人往帶起陣陣風聲。
坐在石獅子上的關七伸手接住了一點落雨,感嘆道:“果然下雨了,這個諸葛小花,跑這麽快,也不給我送把傘來。”
諸葛神侯顧不上給他送傘了,但有別人給他送。
戚少商帶着楊無邪走到了他面前,楊無邪走上前,恭敬地雙手遞上一把油紙傘:“關爺若不急着離開,不妨和我們去樓子裏換一身衣服,梳洗一下,讓樹大夫給您看一看傷勢。”
關七接過傘,揮了揮手:“不必了,哪那麽多講究,剛剛我只是在糊弄他們罷了。”
戚少商嘆道:“關七聖這是故意拖住諸葛神侯和那些禁軍,您知道凄涼王的動向?”
關七悠悠道:“我本也不知道,他襲殺崖餘,若不是諸葛,他就殺了我唯一的弟子,若是他本人出現在我面前,我一定殺他,他怎麽會有那個臉和我再往來。”
他只是剛剛在脫離天心時,往下瞥了一眼,發現了皇宮那邊的動向。
楊無邪笑道:“他沒有再和您聯系,但您适才一定是知道了宮中的境況。”
關七當然知道,他看到長孫飛虹趁着宮中空虛,直入深宮,和自己安插在皇宮中的人接上頭後,直奔趙佶所在之處,抽出牆上的天子劍,脅迫趙佶寫下“罪己诏”。
他沒有急着動手,甚至給了那些宮女太監和侍衛們求援的機會,自顧拖着趙佶往大殿去。
這些年,長孫飛虹沒有離開京城,他藏身牢中,苦思苦修,直到今日天變。
他要在趙氏列祖列宗的面前,将趙佶在位這些年的所作所為一一陳述,當着趕到的文武官員面前,殺了徽宗。
并在殺人後自刎。
實現了他當日對諸葛正我的許諾。
關七笑道:“我和長孫也是多年的朋友,我雖然說要殺他,但這不代表咱們過去的交情就不認了,何況他一生所求,就是做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留千古之名。”
“我今夜已經見到了許多人的道,也成全了他們,何妨多成全一位昔日好友?”
“殿上刺君,以雪國恥,他所求之名,如何不可垂青史、銘世人?”
“臣能刺君,人可敵天。此道已證,亦他亦我。”
“求仁得仁,當無憾恨。”
關七從石獅子上起身,他的傷已經好了泰半,面色平和道:“好一場凄涼風雨,教我如何能煞了風景?”
說完,他沒有再駐留,只是看了看自己被劍氣所損的衣物,覺得也沒什麽遮擋的必要了,幹脆和剛剛來到這個世界時一樣,将撐起的傘放在了剛才坐的石獅子身上,遮住它的半個腦袋。
自己空着雙手,被發跣足、衣衫飄搖地走入了風雨中。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