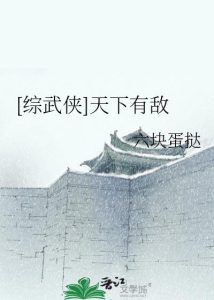迷天 36
米有橋握着手中長棍,一手握拳,在他身後不過五步開外,方應看已經沒有了聲息。
同樣站在他五步開外的,還有持劍的關木旦。
面對吳其榮和詹別野時,關木旦還偶有喜色,可他對方應看從始至終都冷淡得近乎輕蔑,這種态度讓米有橋心中升起憤怒,好像同時被他輕易碾碎的還有他心心念念的另一種人生。
他的想法,他們的想法,關木旦當然無法理解。這位七少爺生來富貴,天資之高曠古絕今,有佳人傾心,兒女孺慕,天下競向,他所思所求從未落空,翻天覆地的偉業也能成就,以他今日的地位,哪怕中道而殂,青史上也會銘刻雲州王所向披靡的功業。
可天下只有一個關木旦!
更多的人不過是在不知終點的路上苦苦掙紮,跌跌撞撞。
能夠走到今天,站在這裏的已經是千萬人中的一個,誰沒有流血流汗,生死裏走過?
他憑什麽否定別人的抱負志向?
“你錯了。”關七忽然開口道,他似乎真的能知道米有橋此刻的想法,卻并未動怒,只是淡淡道,“我不是在否定你們的道路,而是在踐行我自己的道。”
“就像你們為了達成目的而殺的人、做的事一樣,我一開始就說了,我今天是來殺人的,為我的目的殺人,只是這次被殺的換成了你們。”
關七還是願意和這位舊識多說兩句的:“你們為了權利殺人,你們不願意得罪大的勢力,但大勢力外的人你們從不手軟:朝中不願同流的官員,市井中敢于出頭違抗的游俠,黑白兩道上不肯歸附的江湖散人,還有為了守住自己清名而斬草除根的百姓。”
“我也殺人,這三十年來,為了擴張勢力,在江湖道上、東南之地、燕雲二州、西夏北遼,甚至如今的西州回鹘,滅的國家也有,在這個過程中我殺的人有多少,連我自己都數不清,說是屍山血海也不誇張。”
“這些人都該死嗎?也不見得,他們也有父母親人,也是為了自己的勢力乃至國家。”
晚風吹動關木旦白衣如雪,手中長劍如血。
“當我走上戰場時,任何人都可以殺我,我也會取走每個敵人的性命,一如今日。”
米有橋怔了一怔,才搖頭道:“你,真是練武練到瘋魔了。”
關七不以為忤,反而欣然道:“人生在世,總有些執着。各位也深得‘貪嗔癡’三味,這位黑光上人貪于生,驚濤書生癡于美,元先生一生際遇,大多也從一個‘嗔’字中來,方小侯爺三者俱全。”
元十三限聞言冷哼了一聲,并未反駁。
“那米公公你覺得,自己執着一生又是為何呢?”
米有橋沒有說話,他站在夜間漸起的霧氣中,連神情都變得模糊起來,他年輕時就留起的胡子本已發白了,現在卻在發黃,蒼老的眼睛在月下泛起了藍光。
缥缈的霧氣急速向他手中的長棍聚攏,仿佛有一只巨獸張開了嘴,一口要将所有靈氣和殺氣都吞入腹中。
當這些都被吞噬時,天地間只剩下了“空”。
但空只是它的表象,就像握棍的人——他這麽多年的謙和低調、無欲無求,好像所有事都只以官家主人的想法為主,自己只是一個“空殼”,這當然是假象。
潛藏在這“空”下的是一股極端兇殺之氣!
老者猛步向前,騰躍而起!
長棍呼嘯寰宇,帶着幾乎要吞噬地水火風、囊括世間空無的“兇”意,掃向它的敵人。
四大皆空,四大皆兇,摧山裂海,朝天一棍。
這就是米蒼穹對關七的回答。
——————
夜色越來越濃了。
比起北方寒意還未散盡的冷夜,江南的風裏帶着潮濕的青草氣息,這是春來的跡象。
方歌吟一時興起,像年少時那樣上了屋頂,一起帶上來的還有一壺好酒,兩個酒杯。之所以是兩個酒杯,皆因為他知道,等桑小娥送溫小白到斬經堂回來,一定也會上到這兒來陪他。
他們夫妻少年相識,相攜白首,數十年朝夕不離,對彼此再了解不過。
果然,當桑小娥回來的時候,見丈夫坐在屋頂上,訝然失笑後,便輕飄飄落到了方歌吟身畔。
方歌吟将手中的一只酒杯遞給她,柔聲道:“陪我喝一杯吧。”
桑小娥自無不應,她知道丈夫此時心中難過,想找點消遣,桑小娥自己也傷心,但她外柔內剛,在感情上比方歌吟更果決。
這很正常,桑小娥雖然母親早逝,但桑書雲對獨女千嬌百寵,天下第一大幫的幫主能給予掌上明珠的太多了,桑小娥在情感和物質上一直是充足的,她的丈夫又是天下有數的高手,對她癡心無二,數十年來從未對她有一句重話。
對一個精神圓滿的人而言,下決心去割舍雖然也痛心,但只要咬咬牙,還是可以做到的。
可方歌吟不一樣,世人覺得方大俠繼承幾大高手真傳,還有嬌妻相伴,人生美滿,但他們不知道,方歌吟自幼離家跟在師父身邊習武,師父死後返回家中,父親卻又去世,他孤零零游蕩江湖,遇見師伯宋自雪,得對方傾囊相授後,宋自雪也死了,他繼承了蕭秋水的絕學,卻從未見過這位師父,救他于絕境的衛悲回更是早已離世。
方歌吟是個重情的人,偏偏他的一生,都在不斷地失去。
等桑書雲離開後,方歌吟的親人就只剩下了桑小娥,他的精神和情感都依靠着妻子,說桑小娥就是他的性命也不為過。
方應看是他們倆一起撫養長大的孩子,說是義子,但在他們夫妻眼裏,和親生無異。
對方歌吟來說,這是個艱難的決定,所幸桑小娥會一直在他身邊,支持他在情與理之間做下決斷。
已經不複年輕的女子輕撫着丈夫鬓邊白發,自從金人破關後,他越發滄桑了,但在桑小娥的心裏,他永遠都是為了她獨闖少林的少年,她不願丈夫繼續為此傷神,轉而說起了一些讓人高興的事:“風裏的濕氣重,明天只怕要下雨,春雨可貴,今年江南一定又是一個豐年。”
方歌吟知道她的心意,便也順着話題笑道:“是啊,關兄治下清明,沒有了那些貪官污吏和盜匪橫強,老百姓的日子好過多了,如今的江南繁榮太平更勝往昔。”
說到江南的民生,方歌吟毫不避諱,若不是厭倦功名,他大概是世上和關木旦想法最接近的人。這位平民出身的絕世高手從未把皇帝放在眼裏,并不拘對方是聖主、昏君,在方歌吟看來,皇帝也是人,既然是人,那就沒有理由淩駕于任何人之上。
比起什麽天子之說,他更傾向于皇帝是一份職位,只是地位很高、權力很大,對此方歌吟甚至覺得,皇帝的權力太大了,這并不是好事,缺乏制衡;憑血脈傳承也不好,皇帝既然是要治理天下的,那誰做皇帝該由天下人來決定。
方歌吟之所以懶于功名,正是因為看透了王朝運行的規則,不過是将“家天下”一次次輪回,他也相信終有一天,這一切會改變,就像從上古堯舜的禪讓到夏朝的建立,也像最早的人茹毛飲血,到如今身着彩衣、竈有百食。
只是現在還做不到,要依賴一部分人來引導。
所以他一直覺得,關七做這個皇帝,可比趙佶合格得多。
這種想法說出口,只怕自己掉腦袋不說,株連三族、九族都是正常,可方歌吟和關七閑談時,卻将之視若尋常。
如此和時下的思想相悖逆,連桑小娥都曾笑他“狂生”,所以他的朋友很多,遍布天下,他的朋友也很少,不過兩三人。
桑小娥靠在丈夫肩上,舉起手中酒杯:“江南好風景,但願這太平之象歲歲如此。”
方歌吟同舉杯道:“固民所願,天下共向。”
桑小娥笑了一聲,又幽幽一嘆,明月照破長夜,千家萬戶共向,未知那些站在窗前的身影中,是否也有故人呢?
——————
關七對斬經堂張侯的武功是有所了解的,不僅僅因為他年少時曾拜會過張天艾,更是因為溫小白。
淮陰張侯的“風刀霜劍”共一千零一招,是他仗之名震江湖的絕招,卻敗在韋三青的“千一”之下,之後的歲月,張天艾苦思武學至理,終于也将這一千零一招化入一招之內。
這一招,路數輕靈的溫小白沒有學會,但他曾在米有橋手中見過,不過在那時關七看來,張天艾的武學思路不過是仿照了韋三青,這一棍再怎麽也脫不出“千一”的範疇去,而三十年前的米有橋在武道上,更只是張侯的影子。
所以,見到米蒼穹這仿佛凝聚了世間所有無情、不公、殺意而成兇煞一棍時,關七有些驚訝,轉而歡喜道:“你已自成一格,好。”
關七沒有用血河劍,而是伸出了雙手,到了現在,他似乎終于準備動真格了,随着功力運使,那幾乎充溢月色的暈光漫漲,以至于他的發色都變成了銀白色。
但那和月光一樣清冷、明亮的,不是光,是凝練到極致的劍氣!
這劍氣使得關七的雙手如同精鐵、堅不可摧。
他的雙手迎着米蒼穹的長棍上托,足足上百斤的銅棍沉重得幾乎能把人壓垮,随着米蒼穹功力灌入後舞動,棍身隐隐泛紅,燒得滾燙。
更何況,米蒼穹在他的棍上寄托的,正是他眼中不可違逆,無可抵擋的“天意”。
天意無情,世道不公,他一生的坎坷蹉跎,到老也只能做皇家看門守戶的忠犬,都是因為這兇煞逼人的天意!
人說天地之間皆是空無,所以四大皆空,可在米有橋的眼裏,天地之間明明都是殺氣!
是人殺人、病殺人、運殺人,天殺人!殺機洶湧,四大皆兇。
人要如何與命争,與天争?
偏偏關七那雙人的手,穩穩托住了這一棍。
沒有人知道那一刻發生了什麽,只看到關木旦拼雙手和米有橋的長棍相接,兩人連連出招,長棍揮舞時發出的嘯聲頻頻被清脆的碰響打斷,那是關七的手截住長棍的聲音。
功力稍弱的人都已經看不清他們交手的情形了,只有元十三限全神貫注地看着,面上泛起驚人的神采,若不是他秉性自傲,作為習武之人,恐怕已經忍不住動手加入戰局。
此時的米蒼穹已經不再像皇帝身邊溫馴的內監了,他發黃的須發飄動,仿佛一只發怒的獅子,兇悍地追獵撕扯着自己的獵物!
而關七呢?
關七在笑。
幾乎要溶入月色中的人面上泛光,雙眼發亮,嘴角帶笑,哪怕米有橋步步進逼,他在步步後退。
關七當然不是要敗了,事實上他現在在做的事,可能旁人想都不敢想,他從米蒼穹的招式中逆推張侯的“風刀霜劍”,從而摸索韋三青的“千一”是怎樣的武功。
韋三青,自在門的創始人,一位憑自己的天賦問鼎武道巅峰的大家,關七一直十分遺憾,自己沒能見過他,連許笑一和諸葛正我都不知道自己的師父身在何處,又是否還在世上。
因為自在門特殊的規矩,師父傳給弟子的武功,自己不能再用,必須推陳出新,而許笑一的功力被廢、諸葛正我又收了一堆的義子徒弟,所以從韋三青的弟子身上,關七見不到多少韋三青的痕跡。
而三十年前,關七和米有橋交手時,兩個人的境界都不夠。
直到今日。
米蒼穹眼中的天地不仁,生靈在競争厮殺中生存前行,可關七通過這一脈傳承而來的棍法,得以和生平緣悭一面的人遙遙相識。
對方是一個怎樣的人?如何以莫大的毅力和智慧,才将一千零一招的刀劍凝聚為“千一”?
他有着獸一樣的野性和君子的溫文,柔和也豪壯,豪情又幽然,執着狂妄,驚才絕豔,淡泊的浪子本性中,蘊含着深情。
是以經歷“風刀霜劍”,仍求那由“千”成“一”的一招。
關七掌上的招式變了,他從一味的抵擋開始反擊,左手刀法,右手劍法,可刀能發劍氣,劍能發刀氣!
刀非刀,劍非劍,刀劍的界限都在掌上模糊了。
最終,他向米有橋邁出了一步,沒有朝天一棍的驚天聲勢,只是平平無奇地向前遞出一招。
就像當日斬經堂內,韋三青向着張侯遞出的那一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