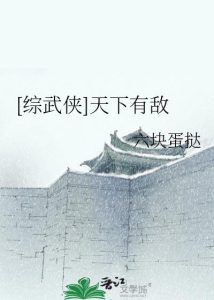迷天 31
汴京城的風起雲湧牽動無數人的心弦,但在燕山邊界上,這些風波并不比一片雪花來得沉重。
日暮天寒,群山飛雪。
時節雖然已經過了立春,但這北方關塞上,依舊不見春風。
擊退了金軍的第三次攻勢後,盛崖餘有條不紊地安排着手下的事,他向來不喜陰謀算計,但在兵法排陣上,卻是個奇才,這段時間他坐鎮中軍,固守雲州,沒有出現半點纰漏。
話雖如此,金兵的戰力強盛,雲州守軍的傷亡不可避免。
雲州鐵騎已經回到了雲州,統一聽從盛崖餘的調度,關七卻依舊留在燕山未歸,與菩薩太子對峙居庸關上。
收到狄飛驚的傳信時,關七正坐在山崖上觀望金軍的動向,在數次攻城無果後,分兵的金國終于停下了腳步,完顏宗望似乎接受了“關七在此一天就攻不下居庸關”的現實,暫時收攏兵力,開始想別的辦法突破這道一人豎起的鐵壁銅牆。
專門送信的鷹隼落在他手臂上,這訓鷹的手段還是他身為公子羽時從金雕部族身上學到的,他幾世的累積并不只在武功上。
數百年裏,他看慣了人事變幻,也不覺得這些消息多麽令人意外。
從之前盛崖餘被長孫飛虹截擊,到這一次方歌吟找到了仇人,要殺蔡京報仇,而在他動手之前,回到京師的長孫飛虹先刺殺了趙佶,諸葛正我因為前遭和他交手,受了傷,在府上養傷,所以這一次長孫飛虹真的差一點殺了徽宗,被大內高手拼死抵抗拖延,等到諸葛小花趕到,才不得不遁走。
趙佶為此大動肝火,因為長孫飛虹是蔡京引薦的,蔡相爺不可避免地被遷怒了,這陣子正自請在家,反倒方便了方歌吟動手,他直入蔡府,殺傷蔡氏麾下的高手無數,擊殺蔡京後坐在堂上,等着人來找他。
可面對方歌吟這番舉動,無論是趙佶還是傅宗書,都保持了沉默,刑部老總朱月明更是一夕間成了瞎子、聾子。
方歌吟等不到來問罪的人,長嘆一聲,帶着仇人的首級,陪妻子離開了汴京,往長空幫舊址去了。
徹底被吓到了的徽宗皇帝,連東南的軍事都放下了,他似乎終于認識到這幾個絕世高手的武功有多高,長孫飛虹險些殺了他,那武功還在長孫飛虹之上的關木旦呢?
趙佶在珍惜自己性命這件事上的造詣,甚至超過了他的藝術造詣。
顧绛看完這通始末後,感嘆道:“他們這些人,過去十多年不見得能出現在一處,這陣子倒是你方唱罷我登場,把汴京搞得很是熱鬧。”
剛剛來到這個世界時,顧绛也曾對這些“青史留名”的人做出過許多計劃,一步步排算如何将他們死亡的利益最大化。
如今他已經不在乎了。死了蔡京還有傅宗書,沒了傅宗書還會有別人,他們會在宋國的官場坐到這樣的高位,從不是個人的意外,是腐朽的官場催生了這樣的百官之首。
百官之首上,還有皇帝,皇帝身後還有整個皇室。
一兩個人的生死,對顧绛而言,已經無關緊要。
紛紛碎玉如時光的碎屑,飄散在漫山遍野,風雪在推動他,當他站得越高,這種推力就越強。
可他已經頂着風雪走到了這裏,他在洪流中積蓄成勢,讓這天下的走向随着他的腳步改變,個人力量的強悍在他身上幾乎達到了極致,是以一人能守一城,一人能成一國。
若再向前走,他是不是就會抵達文明的邊界?
到那個時候,環境不再是支持他的後盾,而是桎梏他的牢籠,突破這桎梏,便是超越世界,破碎虛空。
顧绛的呼吸冰冷,獨立群山之上,明明腳下有兩國千軍對峙,千萬人的命運都懸在這關前。
可他卻覺得天地間除了風雪,空曠得很。
消息上寫着他在此世寥寥幾個朋友的消息,不可避免的,顧绛回想起了過去的那些舊識——任我行、任盈盈、傅紅雪、葉開、李尋歡、阿飛、無崖子、李秋水、掃地僧,還有于神思混沌時相識的燕南天。
他仿佛一直行走在一場又一場的風雪裏,與風清揚在華山的飛雪下論劍,于關外的大雪中遇見孤身前來的魔教教主。
這些人,如今都已埋骨泉下,總有一天,方歌吟、諸葛正我和長孫飛虹也會。
萬山孤冷,天地無言。
大道希微,誰于我先,誰于我後,是非塵土,不過須臾。
顧绛突然伸手拍了拍自己的腦袋,從思緒中跳出來。
自從他成就大勢後,心神常常被天心感染,有“失我近道”的忘情跡象,幸虧他先一步補全了心性,否則大概會很自然地接受這種道染,認同、融入世界的規則,被文明同化,從而滞留于道中,反而難以突破這最大的桎梏。
一生求道者為道所困,聽起來像是個笑話,可古往今來無數人都停在了這一步。
為衆生成道者聖,為道成衆生者佛,為衆生忘道者神,為道忘衆生者魔。
這山下的滾滾紅塵、恩怨情仇編織成因果,因果循環成大道,衆生萬相,誰能窺破天命?
顧绛輕撫着鷹隼被風吹亂的羽毛,望着遠處的金營,倏然發笑,似在笑這場已經看到終局的戰争,又似在笑自己亦不過是這芸芸衆生中的一個。
——————
金國西進的腳步停在了居庸關前,戰局陷入僵持,此時無論是攻城者還是守關者都沒想到,這種僵持會持續上整整八年。
這八年間,西夏在金兵的步步緊逼下不得不西遷,結果關七突然出現在戰場的西線,率領雲州鐵騎,趁金兵立足未穩時席卷河西之地,并聯合草原部落襲擾金兵後方,最終虎口奪食,搶下了這片後世以寧夏為中心,涉及甘陝青蒙的地域,尤其是西夏的馬場和鹽地。
這場西夏滅國之戰,雲州聯合西夏殘部、草原三部共擊金國,戰事綿延六載,關木旦一時間無心東顧。
随着雲州鐵騎與金國騎兵在戰場上鏖戰,攻城器械互相剿殺,金人漸漸發現自己從一開始的上風落下去,有舊遼的臣子說出了這種長期拉鋸戰的關鍵所在。
“金人依舊保持着劫掠的習性,攻城後為了防止被奪回,在城內燒殺搶掠,擄走金銀財物、工匠和婦女,以眼下看,确實充實己方,折損對方,以至雲州雖奪地,也是一片狼藉,但金軍如此行徑,使得西夏之人深恨金人,一心投入雲州,劫掠而來的人口也不好安置,每每于後方騷亂。”
完顏晟也知道這是人心得失上的計較,以至于雲州勢大後,有不少西夏的城池望風而降,卻抵死抵抗金軍,正是因為金人的野蠻作風。
可還未從部落制完成向封建帝制轉變的金國,本就是游牧民族,他們在戰場上厮殺,為的就是財物和人口,你不許他們動,那誰會舍生忘死地在戰場上抵抗雲州鐵騎呢?
當武力失衡時,強大的那一方得以征服弱勢的一方,但若是兩方的武力相當,文明的優勢就漸漸體現出來。
武力會衰頹,文明只要不斷絕,就會繼續傳承下去。
而傳承的關鍵正在于能得人心。
金人不是沒有動過讓宋國攻雲州的念頭,可在宋軍攻雲州時,大批軍士甚至将官拖家帶口轉入雲州之後,宋軍恨不得連夜在邊界線上建起高牆,防止人員向北流失,哪裏還能自己上前去送人?
所以面對金國的國書,宋國每每只敷衍應對,氣得金國使者甩袖而去。
宋國君臣卻自覺十分得意,大有鹬蚌相争,漁翁得利的想法。
自在門舒大坑曾是西軍将領,聽聞此事後向諸葛神侯抱怨道:“前遭攻西夏,為西夏所敗,損兵十萬,後攻遼,為耶律大石所敗,又損兵無數,如今有心功業的習武之人都往北去了,官家居然還想坐收漁人之利?用什麽去收?有哪一處的軍隊能敵得過關木旦麾下虎狼之士、百戰精兵?”
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對沿着邊界線一步步北上,蠶食了西夏、舊遼多地,深入草原諸部的關木旦而言,一旦與金國分出勝負,轉頭南下,輕而易舉。
如今燕地雖然依舊為耶律大石的“北遼”所據,但燕地之人早就心向雲州了,多年來兩地往來密切,兩地本就漢人居多,關七威名震徹九州,他今天說要燕州,明天燕地的官員們就會扔掉北遼的旗幟換上雲州三辰旗,連耶律大石自己都已經磨得沒有脾氣了,就等着關七忙完西邊的事過來。
眼看着雲州鐵騎與金國騎兵要一路在西北針鋒相對,沖入了西州回鹘境內,糾纏個沒完,沒有十年八年分不出勝負時,一道密令從金國中京發出,再一次撥亂了局勢。
——————
逃出滄州大牢的楚相玉死了,他死後引起了連雲寨的一系列變動,但這都是可以斡旋的事,比起他手裏簡王留下的向太後遺诏,他當年試圖借兵金國入宋的路線被手下人帶到了金國,才真正引起這一場提前爆發的兵禍。
這不是無跡可尋的事。
這些年來金國和宋國的貿易被居庸關截斷,常年的戰争消耗巨大,北方本就不如南方貿易亨通,經濟繁華,當初遼國的人才又不斷向西南流失,金國急需一場大勝和足夠多的財物來振奮氣勢,并在日益嚴重的兩派争鬥中轉嫁一下矛盾。
起初,完顏晟并沒有真想打出多大的戰績,他只是想撈一筆,打個勝仗。
金兵繞過居庸關,突破燕州屏障直入宋國境內,所到之處摧枯拉朽,宋徽宗望之喪膽,為了退兵,竟給出重金不說,還把九皇子作為質子送入金營中。
狄飛驚多年前就因為東南戰事停息,而西夏戰事爆發而離京,那時因為趙佶、蔡京先後被刺殺,時局緊張,做掉方應看的事一時難以下手,狄飛驚就暫時放下了此事。
結果顏鶴發和朱小腰在汴京多年,連王小石都出走兩回,戚少商落魄後被引入金風細雨樓了,他們倆還沒搞定方應看,反而在他手上吃了幾回苦頭。
這次宋金之間的戰事,以此結果停息,正是他一手促成的。
對此,方應看似乎也很無奈:“說到底,這是官家的意思,朝中許多大人也不能接受,尤其是九皇子之事,喪權辱國之說紛纭塵上,罵我的人也有許多,但他們不知道,我又哪裏真能影響到官家的決定呢?”
方應看此話的确有幾分真心在,因為方歌吟暴起殺人的事,趙佶對他忌憚至極,于是對方應看這個方歌吟義子也越發親近倚重起來,似乎他只要在方應看這裏做個“明君”,方歌吟就不會突然覺得蔡京能坐到這樣的高位,都怪皇帝提拔,然後跑進皇宮也給他來上一劍。
而且在趙佶看來,方應看實在是個懂事貼心的臣子,在朝臣喊着國家如何如何時,只有方應看更看重他這個官家的安全,金軍逼近汴京,援軍不至,這個時候無論付出什麽,只要能保住汴京,保住趙佶這個皇帝,就都是值得的。
至于榮辱,國之大事,何必在乎一時的榮辱?
一時間宋國舉國嘩然。
西州大營內,得知消息的狄飛驚罕見的啞然失笑:“小侯爺這番舉動,倒教我不知該不該後悔當日沒有殺他了。”
溫純搖頭道:“你後不後悔未知,但方伯伯夫妻二人一定後悔得很。”
就雲州和金國的戰局而言,金國突襲宋國的影響并不大,但并不是沒有影響。
耶律弼摸着唇邊的胡子,冷不丁道:“要不,咱們把這個九皇子做掉,幹脆讓宋國和金國繼續打下去?”
溫純聞言一怔,心想幸好師哥還在雲州,若是他在此——唉,說起來,這個九皇子也算師哥的堂弟,可于趙氏一族而言,親緣又算什麽呢?弟弑兄,父舍子,若師哥能夠選,他也斷然不願生在這樣的家族中。
斡爾幹卻皺起了眉:“宋國能打得過金人嗎?而且,以宋國皇帝的膽子,就算死了兒子,他也不見得就會為了這個兒子開戰吧,只怕到時候,這個九皇子就是水土不服,病逝的了。”
耶律弼想到趙佶,聯想起病死在了西夏撤離途中的天祚帝,發現斡爾幹說的還真有幾分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