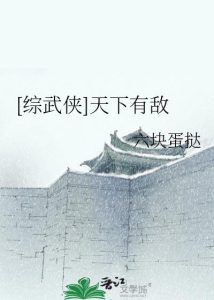于是這一日一日的過去,唐天戈便真的沒有去賢靈宮尋慕瑾。
這入夜之時,獨身于養心殿确是十分無聊的,雖是不得見面,他心中卻是念着慕瑾,于是便揮筆丹青,畫出了慕瑾中秋大宴上那一襲紅妝的模樣。
他對于自己筆下的慕瑾頗為滿意,便将此畫題了字,落了印,心下尋思着将其贈與慕瑾。也算是借此緣由,去探望她一面。
而讓唐天戈未曾料到的是,他還未至賢靈宮,便在這必經之路上碰見了慕瑾的貼身侍女。
“免禮。”唐天戈看着眼前跪坐在地上的若荷,輕聲詢問道:“淑妃可在賢靈宮?”
若荷聽聞唐天戈的話,卻并無動作,依舊保持着跪坐的姿勢:“回陛下,淑妃娘娘确在賢靈宮。”
唐天戈聽罷以後輕點了點頭,正欲明日起駕去賢靈宮,便見一侍衛從不遠處匆匆跑來。
那朝他奔走而來的侍衛,正是梁餘。自打他同唐天戈共同發覺高貴妃異常的那一日起,唐天戈便将其封為了信者。
高欣顏勾奸一事,終是不适讓更多人知曉的。唐天戈亦是顧慮到了這一點,便讓梁餘放下手中的事物,去徹查此事。
可是……出乎他二人的預料,這十天過罷,高欣顏竟然毫無異常。有時候甚是連唐天戈都以為,那日不過是自己看花了眼罷了。
只是當他靜下來細細思考之時,便又會如夢初醒——高欣顏這個人,他不得不防。
那名從不遠處奔跑而來的梁餘輕附在唐天戈的轎攆旁,沖着裏面的人言說了幾句。唐天戈的眉眼便瞬間冷峻了下來。
絲竹看着眼前唐天戈的神色稍有變化,亦是跪在原地,不敢動上分毫。
“起駕,昭陽殿。”唐天戈厲聲言之,語氣是道不明的冰冷。
擡轎的侍衛們聽聞了唐天戈突然下來的旨意,皆愣了片刻,待到她們回過神來欲起轎的那一刻,唐天戈卻是如同待不及了一般直接拉開轎簾,從轎攆上躍了下來。
那幾名擡轎的侍衛見了此狀慌忙的跪下,求饒道:“陛下,奴才知錯。”
唐天戈卻并未理會,他向前渡了兩步,正欲直往昭陽殿之時,望見了一直跪在旁側的絲竹。
絲竹亦是察覺了唐天戈的動作,忙叩首道:“奴婢恭送陛下。”
唐天戈卻是迅速的回過神,從那轎攆之中将畫了數日的畫卷輕輕捧至了出來。
“你既是要回賢靈宮,便替朕将此話交于淑妃吧。”唐天戈輕慢的嘆了口氣,沖着跪坐着的絲竹言之。
絲竹心下卻着實是意外的,她有些猶豫的接過了唐天戈手中的畫,見其神色無恙之後,才緩緩的朝着唐天戈請退安道:“奴婢遵命,恭送陛下聖安。”
眼望着唐天戈離開的身影,絲竹終是松了口氣,從地上緩緩的站了起來。
她的眉眼緊緊的盯着唐天戈交于她的畫卷,思慮了片刻之後,捧着它歸至了賢靈宮。
南越宮昭陽殿
偌大的昭陽殿此時甚是清冷,不見侍衛侍女,有的只是高欣顏和一位蒙着顏面的侍衛。
她坐在床榻之上,左手輕輕的抵在颔下,将右手緩緩的送至那侍衛的眼前,神色不比尋常額淡然。
那蒙着顏面的侍衛心下瞬間領會了高欣顏的意思,快速的将食指與中指搭在了高欣顏的脈搏上。
他的神色随着搭上脈搏的瞬間又些許的轉變,高欣顏将這變化看在眼裏,卻是未再言說。
待到一刻之後,那人輕收起了收手,神情甚是複雜:“依貴妃娘娘的脈象來看,這肚子着實是沒動靜的。”
高欣顏聽聞了此話,不禁的一笑道:“自打那慕淑妃有身孕以來,陛下不是去賢靈宮便是留宿養心殿。不要說本宮在這昭陽殿空冷寂寞,怕是整個後宮,都是如此吧。”
那蒙面的侍衛聽罷,沉默了片刻後方才緩而言之:“皇上對那慕淑妃,确是過于上心了,難怪高将軍亦是将那慕淑妃當成心中一大患事。”
一直神情無恙的高欣顏聽見了父親的名字,微側過頭來,直視着那名侍衛,聲音冷峻道:“我父親說了什麽?”
“這慕淑妃雖是淩國的降俘,在這南越朝堂之中自是無權無勢的。可是她如今懷有了身孕,将來母憑子貴居于後位,也并不是無可能的。”侍衛靜下心來,緩緩地分析着慕瑾身上的種種。
後位?高欣顏的心下異常的波動了一刻。在她平複下情緒之後,聲音亦是愈發的冷靜:“做皇後?她憑什麽?本宮才是陛下明媒正娶的結發妻子!有本宮在這裏一天,她便休想稱後。”
那蒙面的侍衛只是輕緩的嘆了口氣,緩之:“貴妃娘娘着實是陛下的發妻,只是早年陛下心系着報先皇之仇,是不許娘娘懷上皇子的。”
如此一言,卻是戳中了高欣顏心中最脆弱的一根弦。
在她邵華之年,她奉父母之命嫁給了稱皇三年的唐天戈,初入越宮之時,唐天戈對她甚是寵愛。可是少人知道的是,在這宮中每一個花好月圓的深夜裏,唐天戈都與她相敬如賓,未曾盡那夫妻之事。
好不容易到了唐天戈弱冠成年之歲,她與他一朝進了房事。那是她第一次體驗到初為人妻的感覺,她心下既激動又感動,仿佛已是擁有了這世上最珍貴的一切。
然而唐天戈卻毀了她的向往,他将那一碗避子湯賞賜給她,以為父報仇重振南越的緣由,逼迫着她将那湯藥一飲而盡。
那碗避子湯不止斷了年少之時的她為唐天戈産下孩子的念想,亦是将她一顆火熱的心全然冰凍。
高欣顏緊緊的攥住了雙拳,任由着指甲嵌入進手心。
慕瑾她憑什麽?她憑什麽跟自己争?
她不過是唐天戈複仇歸來之後從淩國帶回來的降俘,她憑什麽就可以得到唐天戈的寵愛。甚至,還有了這麽一個孩子。 這是她高欣顏肖想多年的事情,如今卻在另一個身上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