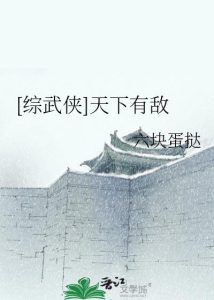迷天 20
長孫飛虹看着盛崖餘,他是看着這個孩子長大的。沒有人知道,哲宗當年其實在交代諸葛正我等人之餘,還将這件事告訴了長孫飛虹,凄涼王是王室之後,如果有一天這個孩子想要拿回自己的地位,僅僅靠諸葛正我這些外臣是不夠的,凄涼王是哲宗為自己兒子安排的後手。
以他宗親的身份來說,當然是希望趙宋的江山穩固的。
農耕文明的基礎紮根在土地上,糧食要春耕秋收,這是一個漫長等待的過程,需要安穩的環境和不錯的天時來保證糧食的産量,這種需求被放大到整個社會後,就是對大環境穩定的渴求,家天下的誕生說到底是這種渴求催生的。
父死子繼,兄終弟及,朝臣可以早早地就知道下一任國家首領是誰,他有怎樣的性格和處事手段,對權力有野心的人也能知道自己的力氣該往哪裏用,只想做事的人只要知道不會因為争奪皇位而發生大的混亂就好。
東周列國之争,漢末群雄逐鹿,西晉八王之亂,唐末五代十國,都是中央權力崩塌後的大亂。
長孫飛虹思考了很多年,起初他覺得就讓趙佶做皇帝,小太子平平安安做個富家公子過一生也很好,他的父親雖然會希望自己的兒子能站在最高處,但為人父母,最重要的,還是希望孩子能平安快樂。
但随着趙佶把朝廷搞得烏煙瘴氣,長孫飛虹的想法開始改變,他想要把趙佶廢掉了,反正小太子已經長大懂事,讓他來做皇帝不比胡搞的趙佶強嗎?至少他會信任賢臣,不會為了自己的藝術追求搜刮天下。
可到了現在,趙佶還會輕易讓出皇位嗎?皇帝的更替必然會引起大的動蕩,偏偏如今女真部落建立了金國,宋與金結盟,要圍攻北遼,西夏也進入了戰局,耶律南仙頻頻扣關,試圖圍魏救趙,攻打宋朝以圖讓宋無暇分身。
諸國烽煙已起,這個時候宋朝能換皇帝嗎?
偏偏小太子在關木旦的身邊成長起來,他的羽翼漸豐了,燕雲鐵騎是一支以西軍和江湖好手起家的勢力,他們在燕雲之地的名聲極好,甚至可以說在遼地漢人眼中,他們的統治力勝過遼人,關七北合草原諸部,西通夏國,與漢人、奚人往來密切,耶律大石據燕州與關木旦據雲州,幾乎分庭抗禮。
比起關七,遼國邊境上的那些山寨不過小打小鬧,楚相玉當年雖然鬧出了不小的動靜,但依舊可以被迅速治平,如今南方叛亂又起,這件事雖然與關七無關,但霹靂堂那些故老能維持到今天,不都是關木旦還不想徹底做絕的緣故嗎?
這一場亂事,關七看似猝不及防,也被牽連到,但他真的毫不知情嗎?他真的沒有消耗大宋國力,最終率兵南下的意圖嗎?
在這件事上,諸葛正我保持着沉默,他依舊努力去懲治惡人,挽救良善,但在這場即将到來的雙龍之争中,他的袖手旁觀本身就是一種态度。
長孫飛虹該怎麽做呢?
他會在這裏,是被人引導的,多年前他曾刺殺蔡京,更因此接觸到了蔡京的弟弟蔡卞,後來因為他的事牽連到山東神槍會,是蔡卞出面保住了神槍會,當然,也因此,行刺蔡相給神槍會惹來大禍的長孫飛虹不适合再掌權了,他們反而會感激蔡氏不計前嫌的恩德,如今的神槍會已經被蔡氏的勢力徹底滲透了。
眼看着昔日的神槍會變成現在這樣,長孫飛虹不是不遺憾的,他知道神槍會本身就有很多問題,門內山頭林立、争權奪利,但那時好歹還在一條正道上,如今走上了邪路,雖是被權力裹挾,但也是他們自己作出的選擇,所以長孫飛虹并不打算去挽回什麽。
各人有各人要做的事,想走的路,他當初刺殺蔡京時沒有顧及神槍會,如今神槍會舍棄他,也是應該的。
但他畢竟曾是神槍會的凄涼王,所以道理上,他因此欠了蔡卞一個大人情,蔡京以此要求他做一件事,截殺關七派回江南的人。
長孫飛虹不知道蔡京是出于偶然,還是真的知道了盛崖餘的身份,畢竟傅宗書這些年都在他手下做事。
而在長孫飛虹跟着盛崖餘一行人走過來時,他心中萌發了一個念頭。
其實現在是個很好的時機,金國、遼國、西夏戰成一團,如果這個時候披露出當年的事會如何?
如果有一個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殺了哲宗的獨子,再借此功勞面見趙佶,說自己所殺的原是趙宋真正的繼承者,趙佶篡權奪位,殺兄弑母,連簡王和出逃的小太子都不放過,是真正的逆賊,助賊者形同叛逆,當天下共讨之,然後将趙佶格殺。
如此,整個宋庭就會亂起來,關木旦大可以以為徒弟讨一個公道為名南下,最好在金國和遼國分出勝負之前,平定天下,在趙宋王室中挑一個傀儡上位,重整宋朝的兵力,以逸待勞,加入這場大争中。
只要有一個人不計得失,無所謂生死去做這件事,并有能力去做到這件事,屆時整個天下的大局都能被改變。
這個人,為什麽不能是他長孫飛虹?
這個人也只能是他長孫飛虹!
因為他的身份,他的武功,他的際遇。
他不想和諸葛正我一樣徒然等待着這場争鬥的結局,雙龍相争的結果又能如何?即便少主登位,不過是又一個趙煦,在君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趙宋,君王也壓制不了這些争權奪利的臣子,就算推行新政,最後也落得一個人亡政息,重走一遍當年的路罷了。
唯有以雷霆手段,才能劈開混沌,教日月更換,乾坤倒移。
大丈夫生于世間,當有所作為,不能名垂千古,也要做他人不能為之的大事!
除此外,世人非議,身後萬丈波濤,都不必在意。
只是這一遭,要對不起關兄、哲宗和面前這個孩子了,他會在格殺趙佶後自刎向他們賠罪。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
即便知道這是一條不歸路,他也要渡河而去,他本就是一個“狂而癡”的愚夫。
所以,他已經下定決心,要殺盛崖餘。
——————
荒野山林中涼風乍起,風中刺骨的寒意,來自于眼前人藏而不發的殺意。
十人近衛已經拔出了佩刀,他們久經沙場,對戰場上的厮殺再熟悉不過,他們也曾配合結陣,誅殺遼夏的高手,而他們的首領更是關木旦親傳的絕頂高手。
位于陣勢中心的男子眉眼清寂,他的樣貌好看極了,不僅僅是俊俏,堪稱清隽絕秀,冷傲如霜,卻也有一種讓人忍不住去憐惜的蒼白寂寞,如青鋒劃破碎冰,殺氣升成高華。
凄涼王其實很喜歡他,喜歡他自幼聰慧過人,武學天賦也高,精于兵法算計,最難得嫉惡如仇,比起關七的超脫,這個孩子身上有和自己一樣的寂寞、執着。
或許血脈的确是有一些影響的,他是這個孩子的長輩,他們倆隐隐有相似之處,包括所用的兵器武功。
盛崖餘早年從關木旦學劍,但劍這種兵器在戰場上施展不開,所以他又改學槍。
關木旦是真正的武學大宗師,一通百通,他和凄涼王交手的過程中學到了神槍會的武學精髓,他以自己的學識為基礎,參考神槍會的絕學,最終根據盛崖餘本人創出了一門槍法。
所以身為關七麾下第一人的盛崖餘以“槍劍雙絕”著稱。
長孫飛虹比那些人更了解他一些,知道他除了戰場上厮殺的功夫,還有一門絕技用以防身,如果覺得在長槍的範疇外就不會被他所傷,那就太天真了,這孩子是個真正的天才,除了槍劍外,他還是一個暗器宗師。
甚至可以說,暗器才是他最可怕的手段,因為槍劍還有跡可循,暗器卻防不勝防,多少高手都在武功不如他們的人手裏丢了性命?
雖然以他高傲堂皇的性格,真正與人對決時,他的暗器手段更像是明器,但在決生死時,他是不會拘泥于手段的。
盛崖餘手中銀槍如洗,這是一位燕地的大匠所鑄造的,槍身上是關木旦以劍氣刻下的七個字,正是盛崖餘自己給這門槍法取的名字——小樓昨夜又東風。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
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說什麽正統、黃袍,南唐後主的這聲悲嘆才是他為自己的結局所做的注解。
——————
化名“田純”的女子坐船上,輕撫着手中古琴,她看着身邊少年手中的潇湘竹簫,輕笑起來,她明亮的眼睛裏似乎有星子墜落,幽幽漫漫:“我哥哥也擅長簫管,他有一支玉簫叫做‘小吻’,我爹還笑他孩子氣。”
“小吻?”笑顏如花的女孩依偎着她,大聲笑道,“那他這支簫也可以叫‘小石’了!”
田純側頭看着身邊的小姑娘,她對于天真的孩子總有幾分姐姐一樣的愛護之心,她自幼見慣了人傑,這樣直白的快樂倒是少有。
紅衣姑娘爛漫地問道:“純姐,你家中還有兄弟姐妹麽?還是第一次聽你說起你哥哥。”
田純眸光盈盈道:“我是父親的獨女,他收有一個徒弟,是我的師兄,和我的哥哥一般。”
溫柔也笑道:“好巧,我也有師兄,這次去京師,我就是去找他的,但他離開師門太早,我和他沒什麽接觸。我爹的徒弟不少,其中倒是有像我哥哥一樣的。”
她捧着臉看着田純,在溫柔看來田純這樣清雅秀美的閨秀,她爹一定是一位大儒學士,收的學生應該也是個文人雅士,會給玉簫起“小吻”這樣奇奇怪怪的名字。
田純含笑不語,她看了溫柔腰間的短刀一眼,神情忽有些惆悵,旁邊的王小石問道:“你提起這位師兄面帶愁色,是怎麽了?”
坐在船頭的白愁飛聞言也看了過來。
田純沒有解釋誤會,只是順着話頭道:“沒什麽,我只是在想,他現在是不是已經到家了,是不是正在和爹爹說話,他們有沒有說起我。”
江上清風徐徐,皎月朗朗,似乎也沒有那麽高遠了。
“師兄的身世凄涼,我爹于他如師如父,他也把我當親妹妹看,是個很好很好的人。”田純端起茶幾上的酒,飲了一杯,和文弱的外貌不同,她的酒量極好,王小石和白愁飛都喝不過她,她斂起袖擺,倚着船邊欄杆,伸手觸及水上的月影,削蔥般的指尖掠起一點水花,擾亂了一輪明月。
她也曾這樣坐過一次船,那一夜江上落雪,父親在船樓上溫了酒,和師哥二人對酌,她披着披風、赤着腳跑過去,父兄都沒有責備她衣衫不整,爹爹只是把挂在一邊的狐裘取下來披在了她身上,她也取了一只酒杯,加入進來。
興致最盛時,她抱着一把琵琶邊彈邊唱,師哥取玉簫合奏,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
當筵意氣淩九霄,星離雨散不終朝。
她就像今日一樣倚在欄杆上回望,忽有行船夜渡,同樣賞雪的人立在船前,他身後站着一個高大的男子,正在為他披上披風,他身子骨還是不那麽好,吹了風微微咳嗽着,似被樂聲吸引,驀地擡頭望過來。
他們幾乎同時認出了彼此,但沒有說話,只是在這大江上同樣行船,同樣賞雪,看見對方。
然後一個順江而下,一個逆流而上。
分飛楚關山水遙。
她停下了彈琵琶的手,師哥的簫聲也變得凄涼起來,萦繞愁緒萬千,只有父親依舊倚舷燙酒,聽完了這一曲,而後道:“當初就和他說,體寒要養,看起來,等這場雪過去,他又要病幾天了。”
關七的目光落在自己的弟子身上,道:“崖餘,情心越盛,越易自傷,他傷在身,你卻傷在心,要學會珍重自己。”
盛崖餘的目光一如落雪,落在槍尖上,他緩緩道:“我出發時就去信給師父,他一定已經在等我回去,許多話您與我都心知肚明,不必再說。”
“如此,只能請您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