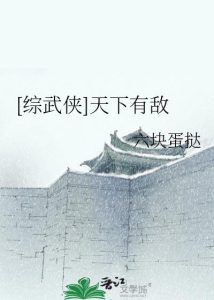迷天 19
入夜的荒山。
盛崖餘倚在一棵樹下,他身邊帶着的十名随從八人也倚靠着休息,一人在高處望風,一人看着馬匹,這是從他兩百親衛中挑出的十人,每個都是關七親手教過的,放到江湖上可以算做一流高手,最難得是令行禁止,行動如一。
他們原本每人都有三匹馬,用以長途奔襲,馬上的刀、槍、弓弩、火器俱全,但進入中原後要低調行事,便只帶了一匹常騎的坐騎來,兵器也只帶了長刀和防身的暗器。
雖說盛崖餘是關七的嫡傳弟子,還是他們的首領,但他們素來相處如同兄弟,十分親近,一人吃完幹糧,直言道:“我多年未回來,這次到江南走一趟,确實繁華,但這樣的好日子我卻過不慣了,只覺得束手束腳,還是在關外來得痛快。”
衆人中年紀最長的青年約有近三十歲,言行沉穩安定,聞言笑道:“薄冰你才多大歲數?就說得上是多年了?”
呂薄冰嬉笑道:“六哥,我本是江南人,出身還算富貴呢,六歲上被人拐到了北方,我今年二十歲,這都十四年過去了,怎麽就不是好多年?”
姜六行也沒有戳中人傷疤的愧疚,他們這些人身上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故事,誠如七聖爺所說,只有現在過得去的人,才有資格和閑餘去說過去,他搗了搗火堆,讓它燒得更旺一些:“關外痛快,那也是對咱們這些人來說,有吃有喝,該休息時也能修整,該動手時就能動手,你換成草原上那些部落的人看看?他們過得是什麽日子。”
盛崖餘聽到這裏,也睜開了眼道:“草原諸部也就是心不齊,否則比遼人更強。”
說到這裏,他們都靜默了片刻,一粗豪漢子開口道:“公子說的是,他們的孩子在馬背上長大,幾歲大的娃娃就能用弓箭,他們的矮馬靈活且耐力強,人和馬一起長大,配合極為默契,他們天然就是最好的騎兵。”
十人中的兩個女子互相依靠着,容貌清麗一些的女子脾氣卻很潑辣:“別說,斡爾幹那些人确實厲害,就是太粗蠻了,除了七爺,他們誰也不服,蕭相景和耶律弼他們都說過,連大小姐他們都只是看在七爺的面子上恭敬些的。”
另一個五官豔豔的姑娘倒是更文靜些:“我聽說,斡爾幹自诩是七爺的獒犬,就像他們牧羊養的獒群,一群獒犬中必然有一只獒王,他們是主人家庭的一員,忠誠且只忠誠于家中地位最高的主人,會為主人看管羊群,撕咬野狼。”
清麗女子翻了個白眼:“他奶奶的,誰是羊,誰是狼?”
盛崖餘聽着他們閑聊抱怨,沒有說什麽,他知道這些議論軍中一直都有,畢竟他們的人太雜了,這幾年和遼國的沖突中折損人手,師父将人打散重整後好了許多,否則就不是一兩句議論了,為了争功,鬧起來都有可能。
尤其是草原部族出身的斡爾幹一衆人,他們生活得困苦,遼人一直壓迫他們,宋人也不見得會接納他們這些“蠻族”,只有師父是這個時代的怪人,他眼中似乎沒有多少民族血脈的觀念,他更看重文明教化和認同感,并不吝于教他們更“正”的道理和觀念,所以斡爾幹才會真心忠于師父,畢竟誰都不是傻子。
融合是個伴随摩擦的過程,比起一味的敵對排斥,他們現在都知道斡爾幹說過什麽了不是?難道這些話是他們蹲在狼騎營帳篷上聽來的?還不是有認識的狼騎和他們說話透露出來的嗎?
盛崖餘沒在意,倒是一直埋頭啃着幹糧的李仲直愣愣道:“我看你是因為斡爾幹上次回了大小姐的話,心裏不痛快。”
鄭十六娘和十八娘是一對堂姐妹,她們素日裏的确和溫純十分要好,十六娘尤其喜歡溫純,她也不避諱:“是這麽回事,我就是看不慣他跟七爺的狗腿子似的,大小姐才是七爺的親女兒,真要論,咱們公子也是七爺的嫡傳,他——”
盛崖餘冷聲道:“十六!”
他的語氣冰冷,十六娘頓時不說話了,盛崖餘卻依舊冷冷地看着她:“你想想斡爾幹立下的功勞,想想他們是七爺的直屬,就知道有些話該說,有些事你連想都不該想,七爺想做的事很多,他救了你們回來,讓你們讀書習武,給你們太平的路走,是你們要追随他的,現在卻要對他的态度說三道四了嗎?!”
是這樣的,盛崖餘心中頗有些倦意地冷嘲了一聲,利益做大後,人多了,心思就雜了,這難以避免,但他不喜歡:“燕雲鐵騎賞罰分明,他只要沒有犯錯,你可以看不慣他的為人,但不該把師父也牽扯進來,七爺是主帥,所有人都應該忠于他,你倒是開始論阿純、我和他了,你想這麽多,幹脆給我回九一營去,醒醒腦子。”
鄭十六娘面色煞白,她咬着嘴唇半跪下,她知道自己失言了,可有些話她還是想說:“公子!我這條命是七爺給的,我若有半點質疑七爺的心,教我天打雷劈,死無全屍!只是——”
盛崖餘冷嗤道:“只是在你看來,親生女兒,親傳弟子,就應該比外來者更親近?哪裏來的應該?在燕雲鐵騎中從來只以功勞論,就算是阿純,七爺也不會在這些事上關照她半分,七爺若是個在意所謂傳承血脈的人,他大可以生上一堆兒子來調教成才,個個姓關掌握權力,可他至今只有阿純一個女兒,還是姓溫,是為什麽?”
“因為他從未有過任人唯親的想法。”
他掃視了一圈所有人的神色,同樣依靠在一棵樹下的青年道:“十六娘出身大家族,根深蒂固的觀念很難改,公子犯不着為了她生氣,她父親就是個寵妾滅妻的,所以她骨子裏就有些‘正統’想法,和咱們這些人不一樣。”
鄭十六娘臉色難看,但沒有反駁,反倒是十八娘道:“雲順,十六姐姐的确有不對的地方,但這種想法能夠根深蒂固,便是有它存在的道理的,堯舜禹德位相繼,最終還是要靠家天下來穩固王朝,這一套雖然讓人不痛快,但勝在穩定,一個大的勢力,總要一個長久穩定的主心骨的。”
雲順諷笑了一聲,本來都快睡着了的少年猛然坐起身,怒道:“你們吵什麽?七爺讓你們讀書,你們讀堯舜,倒是讀出一堆想法來了,燕雲鐵騎是關爺一手創立的,你們要是有什麽‘千秋萬代’的想法,自己和七爺去說,犯得着在這兒和公子爺喋喋不休嗎?!”
坐在樹上的青年悠悠道:“這不是看大小姐的婚約要解了嗎?鄭十六娘的想法明白得很,在她看來,咱們公子和大小姐一起長大,青梅竹馬的情分,要是大小姐不外嫁,那和公子在一起,就是最穩定的繼承人了,她們也喜歡大小姐,覺得咱們公子的為人日後絕不會虧待大小姐,而公子也從徒弟變成了女婿,女婿就是半個兒子,虎豹狼三營的人也該向公子低頭了。”
十六娘厲聲道:“沒錯,我就是覺得,一群人總要分出個主次來的。”
姜六行放下了手裏的樹枝,用衣擺擦着手,沉聲道:“我和公子爺一個想法,這都是關爺的事,他才是主,七爺願意怎樣就怎樣,輪不到任何人來說。十六娘你的手伸太長了,功名心太重,你要是不想做燕雲鐵騎的騎兵,大可以去遼國、西夏找個大人物做家将,慢慢給他們去找主子。”
樹上的何白首依舊悠悠地說道:“我建議你去西夏,如今的諸國中女子要掌權就這兩國阻力最小,遼國後族蕭氏這些年和耶律家關系不太好,奚人和契丹人不是一條心了,但耶律南仙大權在握,繼承人也很穩當,你可以去給她做個心腹。”
呂薄冰笑了笑:“我和六哥一樣想法,我看看,還有小何、阿順、阿仲,小酒應該也是一樣吧。”
又躺了回去的李清酒哼了一聲:“婚事是公子自己和大小姐的事,七爺都不管,你管的倒多,你這麽看重親疏主次,怎麽自己不去投個胎做關爺的女兒。”
呂薄冰笑道:“那看來不錯了,奉哥呢?”
外貌粗豪,心卻很細的劉奉之嘆道:“說實話,我贊同十六娘,七爺的想法自然超人一等,但很多事不能用太超然的态度去應對,因為這世上還是俗人居多。咱們既然要做的是大事業,就該往長遠去想,不能一味想着靠七爺就天長地久,由他來震懾異族。斡爾幹他們應該低頭的,不是為了公子或者誰家的千秋萬代,而是為了穩定。”
十八娘這個時候緩緩開口道:“是,我不贊同婚事,但我贊同十六姐的出發點,公子,這條路咱們其實剛開始,以後會遇見很多事,就像這次錢糧出現問題,或許下一次沒有七爺頂在上面,咱們會獨自面對許多問題,公子為人太過仁厚,導致失去了争的心,可在軍功體系中,就是要靠争才能立足,才能壓過不服和非議。”
呂薄冰想了想,他反對十六娘,雖然十八娘和奉哥說的不無道理,但他也不打算改變自己的想法:“還有誰?魏理兒,你怎麽想?”
守着馬匹的魏理兒悶聲道:“我聽公子的。”
盛崖餘俊美的面容上浮起了疲憊,他們不知道,他骨子裏就反感抵觸這些,不僅僅是因為他的性格,更是因為他的身世。
他記得自己身體好了之後,師父在一個尋常的傍晚對他說的話,從那以後,他就對所有和權力相關的争鬥感到厭惡,他對自己未來的打算,是跟着師父做完他想做的事,如果到時候自己還活着,那就出去走走看看,去結識更多朋友,幫助弱小無辜的人,也很好。
但他更多覺得自己是等不到那一天的,他身上的血脈或許就應該和這個腐朽的王朝一起埋葬。
忽然林中響起一聲長嘆,這聲嘆息是如此惆悵、寂寞,就像一陣晚來的風,凄涼的雨。
原本還坐在各處的人幾乎同時躍起,十人或護衛在盛崖餘身側,或在他身前隔開距離,盛崖餘卻做了個停止的手勢:“長孫叔叔,您怎麽在這裏?”
長孫飛虹就站在不遠處,他背手望着天上有些昏暗的月亮,嘆聲道:“我猜這幾個孩子和關兄相處并不多,所以他們雖然感激七兄,但也覺得一個凡人,遲早要死的。”
這位清貴王孫側目看向那幾個讓盛崖餘去争的侍衛,最終目光還是落在了盛崖餘身上,他的眼神複雜至極,有惆悵、追憶、欣喜,還有淡淡的殺氣:“其實當年我勸過關兄不要管你的事,這本是諸葛正我自己的事情,七兄有雄才大略,何苦承接你的麻煩。”
凄涼王向着衆人走過來,他走得極慢,就像在用腳步丈量他這一生的經歷:“他說,一個人生來如同白紙,父輩的事情不該牽扯到孩子的選擇,既然他願意跟在我身邊,我也喜歡他的聰慧堅強,那他身上的麻煩,我為什麽不能接下來呢?”
長孫飛虹又嘆了口氣:“我把他的話聽進去了,所以選擇了等待,可或許我和關兄都錯了,因為人總是會變的,權力會讓人改變。”
盛崖餘看着凄涼王的眼睛,他明白了對方的言下之意,反駁道:“不,我師父從不會看錯。”
長孫飛虹的神情有些厭倦:“若要單純以事論,很多事是分不出對錯的,你不能說他們就不算為大局着想了,你今天可以趕走他們,明天可以不理他們,但這種想法随着你們建立的功業越來越多,也會越來越深,到時候,你被推着走,也許總要分出一個‘正統’和‘主次’來。”
盛崖餘有些譏诮地笑了一聲:“你是說,宋太祖黃袍加身,奪柴氏江山嗎?”
凄涼王古怪地看了他一眼,這話有兩種理解,在知道盛崖餘身世的兩人看來,這是在譏諷趙氏一族本也算不上什麽正統,江山也是從別人手裏奪來的,他自己有什麽“正統”好說,但在那些近衛聽來,盛崖餘這是在說他們野心漲到一定程度,會推他奪位了。
一時間幾人都神色驟變。
盛崖餘忽笑道:“長孫叔叔,你知道如果我師父聽到這些話,他會怎麽說嗎?”
長孫飛虹靜靜看着他,這位真正的“小太子”心情終于有點愉悅地說道:“推別人上位,不如自己動手,我就在這裏,你們只要有本事,想要什麽,都可以自己來拿。”
“王侯将相,寧有種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