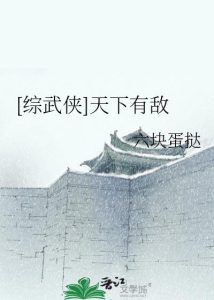道魔 17
在西方的騎士階層被蒙古的鐵騎擊敗後,維護統治的基石被撼動,宗教和政權都出現了分裂,這是西方變革動蕩的開始。
顧绛在游歷期間被卷進不少鬥争中去,一一例數的話倒比在中原時還精彩複雜幾分,畢竟在中原時,他作為魔門的魔師,沒幾個人真敢算計到他頭上,可一個獨行的東方人就不一樣了,尤其是他本人也有些看熱鬧不嫌事大的作風。
當他在西方攪風攪雨、事情結束就易容走人的時候,中原的境況就像是火上煮開的熱水,沒有龐斑這個蓋子後,終于徹底翻騰起來。
龐大的蒙元帝國因過于粗暴的統治手段和糜爛的上層階級快速消耗着它的壽命,因為壓抑的整體環境,還有魔門對正道的打壓,江湖上的黑、道組織快速發展起來,并漸漸擁有了和白道相當的勢力,畢竟在亂世中,活下去成了絕大部分人唯一的目标,而為了實現這個目标,道德和秩序的邊界總會被輕易地突破。
這個時候依舊堅持固守正道,其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這也是龐斑選擇幹脆離開中原的原因之一。
他無心天下,既然如此,也不必和正道之人糾纏下去,而且對他而言,這天下由正道執掌好歹還有一個清平的秩序,确實比魔門搞得烏煙瘴氣好。
龐斑面前的小鍋裏咕嘟嘟煮着,柴火不算幹,燒火時總冒起些黑煙,熏得鍋底也發黑,還有一股木柴燒焦的味道,鍋裏的蔬菜被放在一起炖,說精致,連調味都很少,說粗糙,還能用不同的菜搭配起來。
這鍋炖菜的主人當然不是龐斑,他如今的修為已經溝通了人體與天地的橋梁,按道家的說法就是“餐風飲露”、“食氣而生”,所以對飲食并無依賴,只有想吃時才會用一些。
撿了樹枝來架鍋煮東西的是一個女人,她穿着簡陋的衣物,頭發因為太久沒有洗打成了餅,被用布條簡單地綁着,她盯着鍋怔怔地出神。
這是大篷車裏的女人,龐斑第一次見到她時,她才十四歲,是這一片有名的雛妓,當時龐斑正在處理一只兔子打牙祭,就看到她拎着裙子,赤着雙腳和小腿湊過來,問他能不能分她一點吃的,她可以用東西交換。
龐斑看着這個過早成年的女孩,成熟和天真在她身上糅雜成一種獨特的氣質,這種氣質,他在中原的一些地方也見過,東西方有很多東西不一樣,但在這點上倒是達成了一致。
于是他用一只兔腿和這個小姑娘交換了一串石頭做的手鏈,并提醒她下次不要再相信那個男人的鬼話,這東西根本不是寶石。
穿着潦草的女孩聞言破口大罵了那個客人一頓,邊罵邊吃,還挺有節奏感。
最後這個姑娘給他跳了一支舞、唱了一首歌,說實話,水平很糟糕,龐斑見過那些賢者、貴族身邊的歌者,更是在大都看過色藝雙絕的女子表演,魔門陰癸派一脈的天魔法在聲色上鑽研極深,天命教中七八歲的孩子都不是這唱歌略微跑調、跳舞就會轉圈的水平。
聽到龐斑的評價,她先是呸了一聲,然後支撐不住地笑起來,仰倒在草地上,把自己滾得更髒了。
如今十九年過去了,在得知龐斑要返回東方不再來後,已經面露風霜老态的女子就找出自己能找到的所有菜,炖了這麽一鍋東西,堅持要分給他一碗。
龐斑沒有拒絕這一碗蔬菜亂炖,慢悠悠吃完後,還點評了一句:“你的廚藝比你當初的歌聲還糟糕。”
女子翻了一個大大的白眼,搶過木碗說道:“我就知道,你雖然裝扮得像個窮人,其實是東方某個貴族家裏跑出來的嬌貴老爺!總有許多地方要挑剔,而對我這種孤兒來說,能吃飽就很幸運了。”
龐斑聞言笑道:“我其實也是個孤兒,只不過運氣很好。”
他沒有說謊,身為一個孤兒,現代的他生在一個和平、富裕的國度,能得到很好的照顧,在這個世界,他遇見了蒙赤行,被這位當時的第一高手教導長大,确實運氣很好。
女子嘟囔着,也不說信沒信,龐斑接着說:“當初你用一支歌舞和我換了一只兔腿。”
“是一串石頭手串換的!”女子嚷嚷道,“當時你穿得破破爛爛,我以為你只有那一只兔子,要換你的兔肉,就是索取你僅有的財物,所以我用自己身上最貴的東西和你交換了,可我沒想到那居然是一串石頭!”
龐斑無視了她的抗議,繼續道:“今天我吃了你的送行飯,也該給你一些東西做交換。”
他從身邊的布包裏掏出一個小木瓶,遞給她:“裏面有三顆藥丸,是我做游醫時嘗試藥性做的,你現在跟的那個人飲血練功,體內的氣失衡,你和他一起,難免精氣被他汲取,時間久了,生命會提前枯萎。”
“你們這個地方看起來光明神聖、人人虔誠,撕開僞裝的表層,底下什麽奇怪的人都有,你自己心裏應該也有猜測了,小心一點吧。”
龐斑把木瓶丢給面色發白的女人:“每個月月滿時吃一顆,接下來就看你自己了。”
女人攥着木瓶,疑惑地問道:“你真是個奇怪的人,以你的本事在哪裏都能過得很好,為什麽卻要到處流浪,過吃不飽、穿不暖的生活?沒有妻子、沒有孩子,沒有家。”
“就是因為,我只要願意,就可以過上不錯的生活,所以我才不在乎吃穿,因為極度的自我,所以也不在乎有沒有妻兒陪伴。”龐斑指了指她手裏的木瓶,“就像從一塊木料裏掏出一個瓶子,需要一點點把不需要的部分剝離,最終得到那個木瓶,而木瓶才是我想要的自我。”
“在東方,我們把這個過程叫做‘求真’。”
“追尋真實?”女人抱着自己的膝蓋,她大概明白龐斑的意思,但不太能理解,她沒有接受過教育,一直在生存的底線上掙紮,若非實在對這個奇怪的人充滿了好奇,她都不會去做這些生存外的思考,塑造自我的刀從不握在她自己的手中,所以她一直擁有的都太少太少,無論舍棄什麽都會感到痛苦無比。
對她來說,活着就是真實。
龐斑笑道:“那就祝你長久真實地活着。”
——————
龐斑想過,自己返回中原後認出他的第一個人會是誰,可能是正道中人,也有可能是魔門之人。
結果,他第一個見到的,居然是坐在路邊的大和尚。
已經在歲月中自然老化的鷹緣活佛穿着僧袍,面帶微笑地坐在人來人往的路邊,沒有誰注意到這個奇怪的藏地僧人,只有一個黑衣少年站在他身邊,這個少年俊美得出奇,在顧绛的記憶裏只有邀月念念不忘的江楓能在樣貌上和他相比,連顧棋和無崖子都遜色幾分。
龐斑打量了兩眼這個站姿□□如長槍的少年,他和玉郎江楓的溫柔儒雅截然不同,神情冰冷自矜,只是有些驚疑不定地看着鷹緣。
也不知這神神叨叨的大和尚,和人家小孩說什麽了。
龐斑心情頗好地搖搖頭,走到了鷹緣身邊,也學他一起席地而坐,任由陽光照在自己身上,暖洋洋地熏着人陶陶欲眠。
鷹緣見到他,面上的笑意也深了幾分:“數十年不見,龐先生風采更勝往昔。”
黑衣少年默默看着這個“龐先生”破破爛爛的衣物,髒兮兮的臉,随意大喇喇坐着的姿勢,若非此前見識過這個老喇嘛的本事,他只會覺得這藏地來的喇嘛在胡說八道。
龐斑撐着下巴道:“這是咱們第二次見面了,你特地在這兒等我,必然有個緣由吧。”
鷹緣嘆氣道:“以你如今的境界,完全可以閉關入定,嘗試破碎而去了。”
龐斑睨了他一眼,沒有再追問大和尚的來意,順着他的話題說道:“是這樣沒錯。我這一路向西去,過了十多年混跡民間的生活,一開始我有些不适應,人群給了我拘束感,要在人群中生活,就像要把一只大象壓縮到狼的大小,讓它跟着狼群來去。”
鷹緣點頭道:“你秉性冷淡孤僻、孤高決然,明明身負萬民之運望,有天子相,卻自去家國,割舍下了這一切,要再回到紅塵中,确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龐斑知道他所說的天子相,源自上一個世界“關七”的功業,他在平定天下後安頓好一切,才離去,雖然未登天子之位,可一定會留下帝王名位,但這些并不值得拿出來和鷹緣談論:“我漸漸地習慣了,因為我本就是衆生中的一個,只是性格不同,力量更強。”
鷹緣失笑道:“很多人都不會認同你這個說法,在他們看來,你是天魔降世,魔道化身,無情無欲,早就不是‘人’了。”
龐斑知道,但他并不在意那些人怎麽看待自己:“恐懼源于未知和無力,從而妄念滋生,人本就是動相之一,心念無窮,若能教天下人都知我,那我才真正不是人了。”
“何況我這次回中原,本就是打算了結一些首尾後,就尋一個清淨的地方閉關的,你不也是因此來見我的嗎?”
鷹緣知道,就是因為知道這一點,所以他才在這裏等,帶着一個命中注定要被龐斑影響極深的人:“等你破關的那一日,便是咱們的最後一面了。”
蒙赤行與傳鷹的約定,那時便可在他們兩個傳人身上達成。
這是因果,也是緣。
鷹緣道:“我本以為你會在關鍵時刻需要人來推一把,就像燕飛于孫恩、龍鷹于席遙,也如家父于尊師。可你的道基深厚,自成雙極,道心魔種都已圓滿,無需他人助力了。”
龐斑摸着下巴道:“其實我是喜歡有個對手的,但不是為了去往他們的身上映證自己的道,道于我而言,是自我成就,我尋對手,只是為了能有一個勢均力敵的存在,能互相促進,消解些許寂寞,不至于讓我想要說什麽的時候,無人能夠聽懂。”
說到這裏,他笑起來:“所以你來找我,無論什麽時候,我都是願意坐下來奉陪的。”
鷹緣也笑道:“是。所以哪怕沒有父輩的影響,為這生平的第三面,千山萬水,和尚依舊會來見閣下。”
一時間,龐斑有些遺憾鷹緣舍棄了一身的武功,不能和他切磋一二,但若非願意舍棄武功,鷹緣也不會成就如此純粹的佛心。
龐斑轉向已經聽出他身份的黑衣少年,悠悠道:“你從藏地到中原見我,卻不說是為我,那便是為這個小孩了。”
鷹緣颔首:“他與你也有些緣分,這孩子生平唯獨好武道,和你是一路人。”
龐斑微微眯起了眼睛,看着目光灼灼看着他的少年:“能讓你引他來見我,此子未來的成就必然不低。”
“是,若不是你閑雲野鶴的性子,沒有留在蒙元帝國,建立屬于自己的勢力,再過十幾年,他自己也會去找你。”鷹緣又開始神叨叨起來,“可換做如今的你,那時只怕早已不在人間了,他與和尚因緣頗深,我當成全他。”
龐斑笑中透了幾分冷意:“你不怕讓他來見我,反而毀了他的向武之心?”
這一次,鷹緣沒有說話,那黑衣少年铮然道:“活在天穹之下的人,也未曾因為擡頭便見天高,便放棄青雲直上的想法!”
“我若見道而心生畏懼,那是我之心不誠!”
龐斑看着這個少年,臉上的神情都消失了,只有一派平靜漠然,他緩緩站起身,拍了拍自己身上的衣物,便将衣上的風塵全部掃去,留下一襲青衫,一張白至瑩透的臉,整個人似天工巧匠雕琢的玉像,漆黑的眼睛望過來,只一眼便似高山傾倒,天垂半分,壓在他身上!
少年依舊站着,他不僅沒有退縮,反而上前了一步!
一旁的鷹緣含笑不語,龐斑施施然道:“這一面既然已經見過,我便走了,大都還有一群人等着我。”
言罷,他轉身而行,明明之前還人聲喧嚣的大街上竟寂靜無聲,青衫魔師步履閑适,可每一步都踩在他的脈搏上,偌大的古城,似乎變成了一座空城,連他自己都不在其中。
只有一人獨行,轉眼遠去。
直到鷹緣輕嘆一聲,少年才恍惚驚醒,發現自己依舊站在街邊,人聲如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