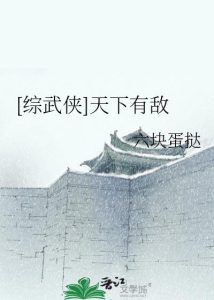迷天 37
千招歸一,大道至簡。
見到這一招,最驚訝的人并不是直面關七的米蒼穹,而是元十三限。
他曾見過這看似平凡的一招,将千種變化融彙其中,非刀非劍,卻有大寂滅,大恐怖!
當年若不是韋三青手下留情,包括張侯在內的斬經堂七位高手,都會同時喪命在這一招之下。
張侯窮盡餘生去追尋這一招,終成朝天一棍,可二人再未交手。
今夜,同出于斬經堂絕學的兩式絕招碰撞在一起。
在關七用出“千一”時,元十三限就知道米蒼穹敗了。
從張侯那一年見到這招開始,從他放棄“風刀霜劍”追求以棍法容納精要開始,從張侯功成之日卻沒有找上韋三青試招開始,就注定了這場敗局。
張天艾一生沒有走出韋三青的影子,“朝天一棍”也不會是“千一”的對手。
韋三青和張天艾的師父是師兄弟,他們同在一位師父身邊習武,本該是最親近的同門,可韋三青的師父丁郁峰卻不被斬經堂中人重視,人人覺得他愚鈍沉默,不成大氣,連去世時都無同門上門祭拜,相對應的,一年後,張天艾的師父龍百謙過世,斬經堂為他大肆操辦,風光大葬,天下英豪都來送龍百謙一程,也為恭賀張天艾繼承斬經堂。
若沒有韋三青名震天下,誰知道丁郁峰已經在沉默的歲月裏,和弟子一起創出了“千一”?
誰知道,“千一”已經勝過了“風刀霜劍”,今日,更是勝過了“朝天一棍”!
張天艾畢竟是韋三青的師兄,他們之間還有梁任花在,雖然梁任花已經看透了丈夫的虛僞無情,和他分道揚镳,甚至故意引張侯出手打掉了兩人的孩子,但張侯到底曾是梁任花的丈夫,韋三青哪怕是為了梁任花的名聲着想,也不能殺張侯。
關七和米有橋不是同門,但他們之間也有一個女人,溫小白。
關七會看在溫小白的面子上,放過米有橋嗎?
不會。
看着米有橋倒下的身軀,元十三限似怒似悲。
——————
許笑一關上了白須園的門。
依舊清雅如同翠竹的男人身上背着出門的包袱,帶了傘,肩上還停着一只小鳥,這是他的“乖乖”。
許笑一已經在這裏住了太久太久,因為自己武功全失、感情失意、朝廷黑暗、奸臣當道,更是因為不願再激化兩位師弟之間的矛盾,四師弟元限對他的誤會已經太深了,他本想化解元限和諸葛正我之間的糾葛,卻多做多錯,以至于今日。
他本已答應了元限,再也不踏出白須園,不會幫助小花,可如今,大廈将傾,他既然已經看到了危局,終究不能坐視。
許笑一知道,這一行很有可能會喪命,他的武功全失,元限卻已武功大成,以這位四師弟如今的性情,絕對會殺自己。
但人生在世,有所為,有所不為。
想必若是師父知道自己的決定,也會支持的。
只可惜,這住了幾十年的白須園,一草一木都是他親手栽種,處處熟悉,處處親切,卻恐怕再也沒有回來的那一天了。在小石頭年幼時,那性情天然的孩子總說,會陪師父在這裏到老,可最終他們師徒倆都回不了故園。
許笑一不想驚動左鄰右舍,趁着月色便上了路,走出園舍,沿着小道向前,寂靜無人的夜裏,他難免心生惆悵,是人離開家的惆悵,就像樹總是不願意被挪離紮根的地方。
忽然,他見到前方拐角處站着一人,那是一個衣着樸素的女子,倚在路邊樹旁,不知已經在這兒多久了。
許笑一沒有看見她的臉,但只是見到她的背影,便認出了對方。
一時間,如墜夢中。
那只會在睡夢中乘月而來的人聽見了腳步聲,緩緩轉過身來,露出一張老去的面容,皺紋爬上了那曾光滑如玉的臉龐,讓她的唇不再似當年紅潤,鼻不再如昔日挺翹,飛揚的眉眼都染上滄桑,雙眸也沒有了年輕時的明媚。
但這就是她,是她。
許笑一張嘴,想要和她打個招呼,問她為什麽在這裏,入夜不歸是在等誰,他心裏當然有猜測,可他總覺得自己沒有這樣好的運氣,也不該有這樣的奢望。
他教給王小石的武功叫做“銷魂劍”、“相思刀”,若不是深得相思的銷魂滋味,怎麽會創出那樣潇灑惆悵的武功,寄存在名叫“挽留”的劍上。
可他想要挽留的,是天上的“織女”。
織就漫天彩霞的仙女來到這人間,青睐于他這愚鈍的人,偏偏命運劃下銀河,傷心離去的仙女便去到了天河的另一邊。
縱有喜鵲搭起長橋,又怎麽挽留不欲再相見的人?
卻聽來人嘆道:“你果然離開白須園了。”
許笑一苦笑道:“你卻不該在這裏。”
織女垂首摸了摸自己的發辮,她雖已早不在乎病症引起的面容老化,可在許笑一面前,她還是會擔心自己是不是顯得不夠漂亮。
明明他們都已經老了。
是啊,他們都已經老了。
多年來因為自己的面容老去,不願意教許笑一看見自己蒼老的樣子,又覺兩人在一處時總多磨難,是命中無緣,所以織女獨自撫養兒子長大,經營神針門,沒有再見他。
一晃數十年了,織女看着面前的男子,因為被廢去功力,沒有自在門的武功護身,他也和尋常人一樣在年歲中老去。但他還是這樣好看,像月下竹林随風徐徐,風骨清徹,甚至比起年輕時更沉穩儒雅。
沒有變的是他柔軟的心性和睿智溫柔的眼神。
織女低聲道:“天衣已經長大,神針門也有人繼承,我沒有別的牽挂了,為什麽不能在這裏?”
何況她深愛着許笑一,即便她心中有怨恨,但她依舊深愛着他,當她得知金人破關而入後,第一時間,她就知道許笑一會離開白須園。
這很危險,他有危險,她怎麽能不來?
而當她見到許笑一時,那些過往的誤會和愁怨也都從她心頭散去了。
許笑一有很多話可以說,說他當年為了化解兩位師弟的矛盾,故意和智小鏡演戲,想讓元限把這件事怪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小花,卻惹得織女傷心,說這些年自己身邊一直有蔡京一黨的眼線在,他不能把妻兒卷入危險中,說京中的境況風雲詭谲,金兵随時都會卷土重來,他沒有辦法保得她周全。
可他沒有說,因為他知道,織女一定已經都想到了,也想清楚了。
所以他只是說道:“太危險了。”
織女聞言發笑:“你的脾氣越發溫吞了,危險?這江湖上何時不危險?何況當年是你對我說,所謂國家,沒有國,就沒有家,現在諸葛正需要你援手籌謀,你可以為此抛卻殘生,我為什麽不可以?我的眼中、心中,就沒有家國嗎?”
“何況你現在這樣,要一路走到汴京,還得我來保護你才是。”
說到這裏,她擡起頭來,神情驕傲,還似他們年少時結伴江湖時那樣,一手神針絕技的俠女總笑這好脾氣的書生一副手無縛雞之力的樣子,竟還想去查驚動天下的大案,若沒有她保護,他一定會被賊人害了。
今日她再來,仿佛時間從未流動,他們還在江湖路上,接下來還要結伴去面對前方風雨。
許笑一驀然發笑,上前牽住了織女的手,也像當年那樣開口道:“好,接下來就拜托姑娘了。”
織女的心跳有些快,這些年她滿以為自己已經心如死灰,可再一次握住丈夫的手,她還是會像少女時一樣心動,她的眼角漾起水光,決然道:“不就是元限嗎?咱們還怕了他不成?!”
生一起生,死一起死,又有什麽可怕的?
許笑一嘆道:“我不是怕他,而是當年的事,我确實對不起他,因為小鏡的心意,我作為師兄沒有一視同仁,而是偏幫了三師弟,欺騙四師弟。”
提起智小鏡,織女恨聲道:“這件事上你雖犯了傻,但你的眼光沒錯,小鏡嫁給他的結局如何?他練功瘋魔了,竟殺了自己的妻子!”
許笑一長嘆一聲,轉而安撫道:“眼下就像你說的,也容不得咱們瞻前顧後了。”
其實許笑一确實無懼于元十三限,他雖然內力沒有了,但武功和境界還在,這些年在白須園全心鑽研陣法,只要讓他擺下陣勢,即便是元限的神箭,他也能破解。
許笑一真正擔心的是汴京城和金國。
織女轉身挽着他的手臂,接過他手裏的傘,還逗了逗他肩上的小鳥,笑道:“走吧,諸葛小花還在汴京等你呢,當年承他的情來為咱們說和,一別多年,也不知他如今怎樣了。”
許笑一提起諸葛正我,不由搖頭:“他這些年勞心勞力,過得十分辛苦,但他這個人好在能自我排遣。”
比起諸葛正我,許笑一更想知道元十三限的現狀,雖然元限已經視他為敵,但他們畢竟曾是同門學藝的師兄弟,元限還是最年幼的一個,身為師兄他本該照顧好他們的。
這麽多年了,四師弟心中的激憤之氣,有沒有淡去一些呢?
——————
元限心中的那股氣從未消減過。
随着年月漸長,男兒老矣,這股生平不得志的憤慨越發濃烈。
他看着米有橋的屍體,那些跟着米有橋的小太監無一個敢上前為他收斂屍身。
米有橋敗在了關七手下,從今以後,他就成了關七生平戰績中的一個說項,沒有誰再在意米有橋的本事,因為他敗了,敗在了關七手中。
元限想到了龍百謙和丁郁峰、張天艾和韋三青,還有他和諸葛正我。
想到他們之間曾也有一個女人,智小鏡。
想起智小鏡,他心中湧起一股撕心裂肺的痛,幾乎要落下淚來。他自知性情激烈,韋三青當年傳他“忍辱神功”,正是要他磨砺性情,希望他能夠“忍”,可惜,他這一生終究不能“忍”。
他不能忍受諸葛正我永遠勝他一頭,不能忍受年華流逝,一事無成,不能忍到身後萬世名傳,生時無人問津!
千秋萬代太過久遠,他就要今時今日的聲名!哪怕是讓天下人畏懼,他也要這令人生畏的威名,成為武林第一人!
為了這個目标,他已忍受、掙紮了太多年。
智小鏡将智高的《傷心小箭》教給他,明确地告訴他自己不愛他,她嫁給元限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報複諸葛正我,為了殺父之仇、負心之恨。
元限知道智小鏡不愛他,她選擇自己,不過是因為對諸葛正我的恨,可沒有愛,哪來這樣濃烈的恨?如果僅僅是因為智高,她為什麽不恨自己?不過是因為她從未愛過自己罷了。
他會愛上智小鏡,雖然也有和諸葛相争的緣故,但他也是真的喜愛這個曾經天真爛漫的女孩,可惜仇恨将她也毀了。
和智小鏡在一起的每一天,元限都在傷心,越是傷心,他就越恨,越是仇恨,想起過去也曾有過兄弟攜手的歲月,就越傷心。
終于,他融合了《忍辱神功》和《山字經》,武功練成的那一天,他用傷心小箭射殺了智小鏡,是恨她,為自己報複她的無情,也是愛她,讓她就此從仇恨痛苦中解脫。
元十三限的傷心小箭由此大成。
此後,他每一次想起智小鏡和諸葛正我,那股讓他近乎瘋魔癫狂的情緒就翻湧上來,成為他箭上的意志,使得他的神箭每出必中,中必穿心!
元十三限的手已經摸上了箭筒,他的箭筒裏有十支特制的箭,其中還有一支紅色的小箭,那是他留給諸葛正我的,所以他沒有取那支箭。
取弓,搭箭,拉弓。
他的意念已經鎖定了月下仿若神人的關七,幾乎在被他意念鎖定的瞬間,原本神色寂寥的關七就猛然擡頭看過來。
元十三限的箭已上弦,已經遍是屍首的院中忽然響起了蟬聲。
月色清冷,寒蟬凄切。
元十三限默念着目标的名字,将箭矢對準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