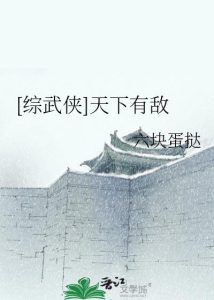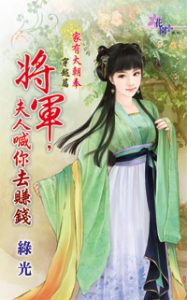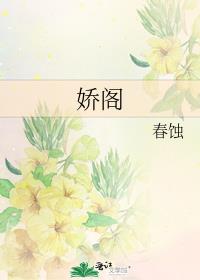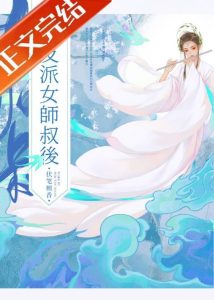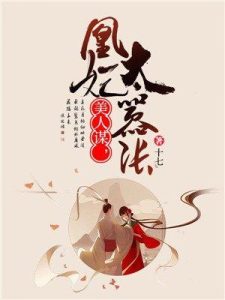迷天 38
顧绛在金國時雖然遇到了不少高手,但他依舊是失望的。
金人至今沒有擺脫部落的習俗,這注定了他們更注重生存而不是精神,在武學上他們追求獵殺的效率,有術而無道,只有金國的一位國師深得自然之理。
宋國的武林就熱鬧多了。
顧绛在殺死米有橋時,甚至有些可惜,若是米有橋不是這樣沉浸權術,那他或許能夠将“朝天一棍”推得更進一步。
任何一門武功都是在繼承者手中不斷更新推進的,一條通天的大道,一定是一代代人去壘砌它的臺階,才成就它的高遠深厚。
顧绛自己就一直期待着,有人能夠沿着他留下的道路更進一步,哪怕是全盤否定,也好過一動不動。
所以他自己也偏愛那些奇妙難練的功法,想要去探究其背後迥異于常人的道理。
不見其廣,何成其厚?
今夜他見到了詹別野的“死境”、吳其榮的“聲色”、衛悲回的“悲歌”、米有橋的“朝天”和韋三青的“千一”。
現在,他想看一看元十三限的“傷心”。
所以在感覺到那鋒銳的箭矢瞄準自己時,顧绛的反應任何人都未料到,他不僅沒有閃躲,還上前一步,迎着這以“百年憾恨、千千情思、萬般傷心”造就的一箭。
顧绛能感覺到張弓的人和他手中的箭矢已經融為一體,這一箭就是元限,元限就是他手中的傷心小箭。
對諸葛正我,對智小鏡,對每一個站在他面前阻擋他的人,對一直在妨礙他達成目的的命運,所有的悲憤恨憎、屈辱辛酸交織成千萬層的浪濤,淹沒了他心底那一縷留戀。
元十三限的弓已拉滿,他并不恨關木旦,雖然關木旦的成就和名聲在他之上,是真正的武林第一人,但關木旦和他從無交集,便無交情,離他太遠,他只知道關七是諸葛正我的朋友,如今是他的敵人。
心已定,情即發,開弓沒有回頭箭。
傷心小箭攜帶着莫能阻擋的氣勢,直取敵人之心,這本就是一門傷心的絕學。
有情之人就無法躲開這一箭。
蟬聲越來越急促、凄切,原本被“朝天一棍”抽空的環境變得越發壓抑,天上烏雲不知從何處來,遮蔽了月亮。
顧绛忽覺一陣惆悵、心痛。
有諸多故人身影在他心中瞬息生滅,往事紛紛,如煙如霧,每一次他走入人世時,同路的人都會與他并行一段,每一次他選擇告別時,留戀不舍的人都還在他身後盼望。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
哪怕是過去情心不足時,他也是有感情的,只是不如常人豐沛,不能體會情愛,也從未感受到極端激烈的情緒。
如今,一種他自己都陌生的感受,被那股“傷心”之意引動,成為箭矢鎖定的目标。
情感似乎成為了他此刻的弱點所在。
顧绛沒有去壓抑這股情緒,也沒有阻攔箭矢,任由它迎面而來。
傷心小箭,正中心口!
——————
聽到帳外的笛聲,溫純一時興起,取下了自己的琵琶。
懷抱琵琶半遮面,比起琴瑟簫管,這種唱見于歌舞演藝的樂器總有一種旖旎氣質。
但溫純對琵琶的第一印象,來源于一位西北大漢,那漢子抱一把鐵琵琶,琴聲铿锵,有金戈慘烈之聲,父親對他們說這位多半是從軍中出來的,只有見過戰場的人,才能作此聲。
回來後,溫純便對父親說,自己想要學琵琶,關七答應了。
溫純本以為父親會為她尋一位樂師做老師,沒想到關七竟買了一把琵琶回來,親手教她。
“學樂器沒有什麽訣竅,無非多練,等你練到一定火候,懂了樂理,自然能操控自如。”看着圍着自己的兩個孩子,關七敲了敲琵琶的腹部,笑道:“到時候,我帶你們做一件你們自己的樂器如何?”
在溫純的記憶裏,父親近乎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他能教師哥笛簫竹管,帶着盛崖餘乘風上山,聽聲取竹節做簫管,也能幫她選适合的琵琶弦,一根根繃緊調好。
這把琵琶就是關七親手為她做的,從她開始學藝就斷斷續續地做,有閑暇又有心情時就取出來鑿磨,歷經六載才制成。
溫純給這把琵琶取名“青凋”,極為愛惜。
何英見她取琴,有點好奇:“小姐,聽他們說,您的琵琶是關爺教的,他們在西夏時曾聽關爺親手彈過,是也不是?”
見溫純點頭,何英追問道:“那一日,關爺彈的是什麽?他們都說是沒聽過的曲子。”
溫純撫摸着琴柱,回想起那時西夏國滅,耶律南仙自刎宮中,父親替她收斂屍身後,按刀觀望着金兵壓境,即将生靈塗炭的銀川城,在耶律南仙墓前彈的那首曲子,低聲回道:“國滅身隕,悲涼無限,父親那一日所奏的,是《霸王卸甲》。”
說着,手指劃過琴身,發出一聲脆響。
——————
顧绛反手拔出了這枚特制的小箭,鮮血從傷口湧出,瞬間染紅了白衣,他封住自身穴道止住了血。
這是顧绛今夜第一次受傷見血。
可元十三限并不為此得意,他的面色一沉,道:“你竟故意硬接我的箭,是看準了我殺不了你?!”
顧绛打量着手裏的箭矢,嘆道:“也沒有那麽輕松,我全力護住了心脈,依舊被這箭上的傷心之意所傷,攻人以‘情’,當真是好功夫。”
“可惜了,你的《山字經》和《忍辱神功》看似融為一體,其實還未真正大成,否則我絕不止受這點傷。”
顧绛捂着胸口的傷,以他如今先天境界,□□幾乎與自然融為一體。刀劍縱是劃開空氣,刀劍過後,空氣總會再填補起空缺,他也一樣,只要對方傷不到他的元氣,讓他的真氣不能運行周天,這種外傷,只要運功很快就自我愈合了。
傷口雖然愈合了,但箭矢上的傷心之意卻留在了他的心口。
顧绛看向元限道:“還不夠,你現在還差一步。”
“理為天地之則,情為人心之源,這是一條大道。”月下人白衣上的血色如同紅梅映雪,白者越白,紅者越紅,明明分明的兩種顏色卻仿佛天然一體,相映生輝,于是這傷落在他身上,也不顯得狼狽了,反而風采更盛,“情既然以人為基,何托于箭矢?”
元十三限沉默不語,只是再一次彎弓搭箭。
這一次傷心小箭沒有射中目标,不是箭失了準頭,而是顧绛揮手間發出了一道劍氣。
無形的劍氣撞上了有形的箭矢,箭身頓時崩裂化為齑粉。
這一箭,落空了。
元十三限皺眉,他沉思了片刻,再一次拈弓搭箭。
箭會被碾碎,是箭上的功力不夠深厚、意志不夠堅定,是因為箭的痕跡被捕捉到,箭矢的速度還太慢!
所以他一箭快似一箭,一箭重于一箭!
元限的面色泛起金色,雙眼卻越來越紅,唯有雙手穩如泰山,不見半點動搖。
可這些箭沒有一支能傷到關七。
元限身後的六合青龍幾乎秉住了呼吸,他們悄然後退,和元十三限拉開了距離,不是他們有什麽其他的想法,而是元十三限身周的氣息都在這連發的箭矢中森然起來,只是站在他身後,便感到渾身發冷,心中恐懼。
身為元限的徒弟,六合青龍對師父這些年性情的變化最了解不過,《忍辱神功》讓他的心思越來越偏激,《山字經》更是使得他的心性越來越扭曲。
如果說早年的元限頂多是不服氣諸葛正我勝他一頭,想和諸葛分個勝負,那到了現在,他已經徹底入了魔,待人無情,為了達成和諸葛正我作對的目的,甚至可以無義,只要妨礙他的人,他都要殺掉。
六合青龍心中對他的敬畏,也漸漸變成了膽寒。
眼見得元限為了傷人而不斷自傷心神,神情冰冷癫狂,六合青龍的第一反應并不是上前幫忙助陣,而是離這位恩師遠一些,不要被他誤傷。
這一退,獨立在前的元限氣勢越發酷烈起來。
顧绛和元十三限都沒有管六合青龍,以及此刻立于牆頭屋檐上的圍觀者,他們有的來自于金風細雨樓,有的是諸葛神侯門下,還有刑部的官員。
沒有人敢上前涉入兩人的較量中。
烏雲将整個天空都籠罩,黯淡的星光都照不亮的深夜裏,神通侯府的燈火搖曳。
元限的箭筒裏,只剩下最後一支紅色的小箭,這是他用來殺諸葛神侯的,此刻也被放到了弓弦上——諸葛小花此刻多半已經被招進了宮中,關木旦卻就在眼前,過不了這一關,他也沒有機會再找諸葛正我了。
随着紅色小箭上弦,元限的面色由淡金轉為紫紅,眼角隐隐滲血,而後他松開了手,然後這支紅色小箭消失了。
在所有人的眼中,這支箭就這樣失去了蹤跡,好像從未出現過一樣!
顧绛垂眸一笑,揮手一拂,右手中指掐住拇指,劃到當胸,做了一個佛禮,指尖拈住的還有那支不見了的紅色小箭。
大梵天王,以花獻佛,是為求法,佛祖拈花,遍示靈山,迦葉一笑。
正是佛門禪宗真正的絕學“心印法”,不為對敵,只為以“心”印“法”。
顧绛開口道:“天王向佛求法,以花寄之,将花易法,則花為法,觀花得法,求之緣起,一笑性空。”
“你将緣系于諸葛,将情系于亡人,将意志凝在箭上,是緣起,此因緣心起,則本性皆空。”
元十三限則冷聲回道:“佛學,是大智慧。但即便是佛學,也得承認,性空不是空,緣起方成世界,因為人生這種種因緣,才有了‘有’,若沒有‘有’,何來‘空’?”
顧绛攤開手掌,将紅色小箭向元限展示:“這是‘有’,那,你的‘空’在何處呢?”
元十三限猛然用右手掰斷了左手一根手指,充作箭矢,急發而出,厲聲喝道:“在此處!”
以花求法,花便是法,以有求空,空就是有。
是名世界。
顧绛終于退了,他足下一點,折身而起,閃躲那突兀出現在他心前的斷指——不,是箭矢。
但在他騰躍而起時,那箭矢也跟着折轉方向,緊追着他破空而來!
顧绛身處自然環境中縱橫自如,第一次感覺到自己身處的空間都被鎖定了,以至于他避不開這一箭,甚至無法從大周天中抽取力量來阻擋它。
他臨空一滞,體內劍氣轟然爆發,一時間這被封鎖的空間內全是洶湧澎湃的劍氣!
先天破體無形劍氣。
顧绛用出了這一世真正的武學根基,激蕩的劍氣如塵埃野馬,浩蕩川流,穿透了沉沉夜色,引九天月華垂落。
面對這無法閃避的一箭,他推出了一掌,劍氣使得斷指在他掌中消融,可斷指內的指骨還是一往無回地刺進了他的掌心!
顧绛笑着拔出了這一箭,道:“好!還差半步。來,來!我來成全你這最後半步。”
言罷,他落到了元限身前,一掌擊向對方胸口,元限亦出一拳,悍然錘向他,拳掌相交無聲,腳下卻地陷三尺!
元十三限須發皆張,情态已狂;顧绛面帶微笑,眼神空明。
他眼瞳深處的重孔再一次張開,對上元十三限血紅的雙眸。
元十三限已經陷入癫狂的神思中,忽有人道:“你半生攀登,總覺得諸葛正我先你一步,所以你的道路狹窄到只有他一人,他若死,你一切成空。”
元限毫不猶豫地回道:“高山本就是越向上,越狹窄,山巅從來只能容納一人,他若死,我便在山巅,這就是登高之路!”
那聲音又道:“這不是登高之路,是登山之路,山有多高,你有多高,可山不能及天高,此路能通天否?”
元限怒睜雙眼,望進那雙重瞳裏,卻恍惚見到自己年少時的情形。
韋三青領着四個徒弟趁着雨後秋涼,踏山游覽。葉哀禪的性子疏懶,總是墜在最後,也看護着三個師弟,元限昂首緊跟在師父身後,諸葛正我和許笑一總有說不完的春花秋月,兩人并肩看着路邊草木。
少年時的元限聽到身後兩人絮叨,不耐地轉過身,喊道:“你們走快點啊,怎麽還在後面,這樣何時才能到山頂?”
許笑一好脾氣地笑道:“哪裏是我們走太慢,是你走太快了,再說,到不了就到不了嘛。”
諸葛正我也跟着笑起來:“是呀,到不了,咱們就下山回家。”
這一絲溫情還未漫上心頭,便被記憶的主人毫不留情地撕裂,他回憶過去太多次了,他已經不會再去回想那個天真無憂、還未經歷失意打擊的自己。
人生如同弓上箭,箭出無悔,也不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