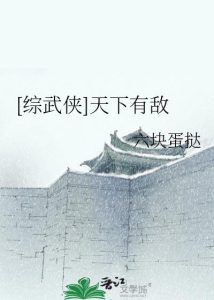迷天 32
蕭相景正搬弄着手裏的機關,這是班家最近新研究出的袖箭,班家本就是延續公輸班一脈,比起墨家的擅守,班氏更擅攻,他們家過去在江湖中制造的器械都是适合個人用的小東西,可機關術真正能展現所長的地方,是戰場。
武林諸世家中,班家才是最早舉家投入關七手下的一族,班搬辦一心重振班氏的威名,為此殚精竭慮,如今也的确如他所願,班氏所創的機械在戰場上幾乎對金國形成了碾壓之勢,金國軍中無人不知班家大匠的名諱。
蕭相景尤其喜歡從班搬辦手裏拿些好用的機關來試用。
不過和班搬辦關系最好的還是關木旦,在此之前誰都不知道,這位名震天下的武道宗師、迷天盟聖主居然也是個機關陣法大家,班家的子弟自幼浸淫此道,能比得上他的人都寥寥無幾。
也不止是機關陣法,天文地理、琴棋書畫、農耕水利、易容醫藥等等,這世上好像就沒有關木旦不懂的東西,別人一輩子都學不精一門學問技藝,他卻無所不通,是以關木旦手下的人無論文武,無不佩服他的淵博。
反正蕭相景是真敬佩,這世上居然能有這樣的人。
和背後有草原部落的斡爾幹、代表了一部分契丹勢力的耶律弼不一樣,父親是漢人、母親則是黨項人的蕭相景平日裏八面玲珑,但他才是一心只聽從關木旦安排,無所謂權勢名利的。
蕭相景自知謀略不足,比起盛崖餘、溫純和狄飛驚這些人,他只能說頭腦平平,所以在這種場合不太開口,除了提需求時,都只聽着。
反正最後由關七爺做決定,關七說怎麽做,他就怎麽做,別的他一貫不去多想。
眼下關七卻不在大帳內,他甚至不在西州。
當金人越過燕山的消息傳到西州時,他就動身南下了,可惜西州距離燕州太遠,一來一往,等他回到燕州時,金軍已經和宋國達成了停戰協議,金人裹挾着這次攻打宋國所得的戰利品,從海上折返金國。
十餘年過去,顧绛再一次踏上了宋國的土地,見到的卻不再是昔日太平景象,被金人攻破的城池一片狼藉,因為宋人的富庶、人口的衆多,軍備卻疲軟,經年與北遼、西夏、雲州交戰的金軍士氣大盛,縱兵厮殺,入城不封刀,所過之處一片焦土,沿着金國所行軍所至的路線走來,戰禍之酷烈,觸目驚心。
只求自保的望風而逃,堅持固守的死無全屍,高樓傾頹,繁華成灰,城內十室九空,城外亂屍成山。
在麻木失神或痛哭不已的人群中,早已看慣了城破後情形的顧绛神色平靜,他身後跟着一個青年,穿一身孝服,懷中抱劍,一言不發。
這個姓孟的男子是顧绛在邊境上撿到的,他會注意到此人,是因為孟殘山當時正拖着一個金人士兵的屍首,他見到顧绛時也只是看了這突然出現的人幾眼,就繼續做自己的事了。
有趣的是,孟殘山并不是江湖中人,他甚至不是一個武人,他是一名文官。
這邊城中的一個官員本是中原人,被派到這裏做官,以他不過二十四歲的年紀能中舉做官,也是個有才之人,曾從名師大儒求學,最難得的是他處事踏實,在邊城裏做了不少實事,和城中百姓相處得十分融洽。
如今,這一切都不複存在了。
“古有召父杜母,稱官員慈愛如父母,可這城中百姓以身護我,城破時,衆人将我打暈後藏于暗道,才茍延殘喘,諸位賜我殘生,當為我父母。”
所以孟殘山換了一身孝服才跟着顧绛上路。
他的本名并不是殘山,只是從爬出暗道的那一日起,望着滿眼殘山剩水,他就叫做“殘山”了。
顧绛并沒有對此說什麽,帶着想要回京彙報的孟殘山從邊城一路走來,直到汴京。
可迎接這邊城“幽魂”的卻是金人得賠款、擄掠無數後北歸,宋國未曾派兵讨還血債的消息。
宋國的統治者根本不在意他的子民遭受的一切。
孟殘山平靜地接受了這個現實,他沒有去見自己的老師故交,而是獨自北歸,臨走前,顧绛終于問道:“宋國邊境上的官員,無不知曉我的身份,你應當也知道。”
對方點頭道:“是,見到您的第一眼,我就知道閣下的身份,所以我并不擔心您會對我出手。”
顧绛道:“那你應該知道,要報仇,跟我回去才是最直接的辦法。”
孟殘山道:“投靠雲州王确實是一條路,但朝依桀纣,暮投堯舜,不過是将性命和公道托付于不同的人,結果如何全看對方的為人如何,百姓的存亡系于朝堂諸公和皇帝的一念之間,然而聖人有雲‘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該如何履行君臣之道,我已看不清,眼下并不想再尋一位主君。”
“何況,我總是不甘心,得試一試,自己去讨這份仇。”
顧绛笑道:“那你的武功着實不太行,除了一點防身的本事,無論是內功還是招式,都稀松得很,在這亂世裏要站住腳,這樣可不太夠,我教你一點東西,你自己領悟,能悟到多少,日後又能不能報這份仇,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
送走孟殘山後,顧绛在汴京城裏逛了一圈,金風細雨樓裏蘇夢枕和王小石都不在,他們據說是去追殺金國高手,追回一些被擄走的宋人了,樓裏只有戚少商鎮守。
顧绛聽說過戚少商的名聲,他年少時跟随雷卷建立“小雷門”,後來他離開雷卷去到邊塞上,奪下連雲寨,成為一方勢力,以抵抗遼兵為主,因為被楚相玉卷入“逆水寒”案,傅宗書下手要他性命,連雲寨被破,他得衆人襄助,才一路逃出追殺。
因在途中偶遇王小石,得到他的助力極多,又有蘇夢枕從中斡旋才平息這場災禍,戚少商感念這份雪中送炭的恩情,接受金風細雨樓的邀請,加入了樓中,取代之前白愁飛的位置。
這位九現神龍的本事不小,也曾傲氣驚人,只是這番磋磨實在消磨了他太多心氣和精神,息紅淚又在他浪子回頭時,選擇放棄和他再續前緣,而和郝連春水在一起,感情事業雙失敗,讓他的自信心落到了谷底,頗有些動彈不動的意思,留在京中守家正好。
孟殘山、戚少商,這京中笙歌依舊,但多了許多傷心人。
在朝中大臣們開始用“漢高祖之白登、唐太宗之渭水”給徽宗的臉上貼金時,更多的百姓則被這場劫掠吓到惶惶不可終日,有心殺敵的北上雲州,只圖阖家平安的倉皇南下,只有無力離開故地的人還在念着“蒼天保佑”。
可蒼天從不會庇佑任何人。
“此等行徑無異于開門揖盜!任由金人踐踏我國土,殘害我百姓,卻不做任何抵抗,這樣會得到那些大人們想要的太平嗎?不,這只會讓金人覺得我宋國軟弱可欺,一次又一次地侵襲,一如昔日的匈奴,甚至是五胡!”
“你也想太多了,不過是把遼國換成金國罷了,這麽多年,咱們怎麽和遼國相處的,從今往後就怎麽和金人相處,一味嚷嚷着打仗,咱們打得過誰啊?是打得過遼國,還是能勝過當初的西夏?和金國交戰,徒增傷亡。”
主戰、主和,議論紛紛,有人選擇離開靠不住的朝廷自己探索前路,也有人趁機依靠背後的勢力攝取利益,發國難財。
戰火将至,亂相已生。
顧绛轉着手裏的酒杯,這宋國就像一座雕梁畫棟的老宅子,誰都知道房子老了,主人又不争氣,不肯耐心呵護,還成天拆了東牆拆西牆,但這個屋子還在,許多人都靠它片瓦遮頭,風雨不會吹進來,日子勉強能過,也許等如今的主人家走了,新主人會好一些。
但這奢侈成性的主人還未過世,惡鄰就上了門,這本就不穩的屋子搖搖欲墜,屋檐下生活的人也見大廈将傾。
顧绛耳邊仿佛聽見被蟲蟻啃噬蛀空的梁柱在緩緩傾倒的聲音,而已經見識到鄰居家的繁華和軟弱可欺後,惡鄰會再一次登門,下一次來,他們就不會再只是抱着撈一筆就走的心了。
他們會想要成為這裏的主人。
顧绛其實并不在意這屋子的主人是誰。短的說,一個人的壽命總是有限的,江山卻依舊;放長了說,封建王朝總有興衰滅亡之時,從未有真正傳承萬世的皇朝。
炎黃一脈不是沒有被其他文明打敗過,五胡亂華、南北兩朝、五代十國,但這些文明碰撞後,都刻入這片土地的歷史中,若站在時間河流的下游去追溯過往,也可以把這個過程稱為融合。
以血脈,以民俗,以言語,以教化,以戰争。
在顧绛生活的時代,民族可以是一個人文化的底蘊,卻絕不是區分彼此,互相攻伐的理由,更不是仇恨和分割的源頭。
只是眼下的時代,距離那個遙遠的未來,還有一條漫長的道路要走。
在這個時代,毀滅和重建才是主題,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間的戰火會将所有陳跡都焚毀。
顧绛飲盡杯中美酒,這神通侯府的珍藏确實不錯,比起北方的烈酒燒心,這些精心窖藏的陳酒香醇清冽,回味悠長,後勁十足。
坐在神通侯府的大堂中,顧绛身邊站着的守衛婢女都僵立着一動不動——全被點了穴道。
燈火通明的侯府中半點人聲都沒有,仿佛一座空宅,寂靜得可怕。
顧绛摸了摸自己腕上隐隐發燙的白玉镯,沒有管它,繼續等此地的主人回來。
——————
不久後,神通侯方應看從宮中赴宴回來了。
自從蔡京去世後,傅宗書繼承了他的勢力,比起老練的蔡京,傅宗書的手段的确弱一點,後來因為逆水寒一案,他又被徽宗過河拆橋,趙佶為了安撫手握遺诏的戚少商,把連雲寨的慘案和一路追殺的血債都甩到了傅相爺的頭上。
傅宗書手下最得力的高手九幽神君被戚少商一夥人所殺,他又拉攏了元十三限,并對金風細雨樓下手,導致王小石為了保全樓中弟子,答應為他去刺殺諸葛神侯,卻反手射殺了傅宗書。
殺了人的王小石在蘇夢枕的包庇下,腳底抹油跑出了京師去到東南,直到事情平息才又溜回來。
在這個期間,方應看漸漸成為趙佶的心腹,他依靠米有橋,籠絡黑光上人,還幫助雷媚聚攏和金風細雨樓不對付的人,其中包括驚濤書生這樣的高手,竟漸漸有了聲勢。
而這一次和他一起回府的人中,竟然還有元十三限,以及元限的徒弟六合青龍。
自多年前方歌吟殺蔡京一役中,元十三限被方歌吟打傷,還損了六合青龍中的兩人後,他已經多年沒有動靜了,如今再現身,竟然成為了方應看的座上賓。
要知道元十三限和方歌吟有深仇,以元限的心高氣傲,被方歌吟重傷後,一心尋他報仇,如今卻和方歌吟的義子混在一起,為什麽?
顧绛嘆道:“若不是我來得突然,都要以為方小侯爺這番陣仗是為了殺我呢。”
他望着一路走來面色僵硬的白衣王侯,道:“想來,我是替方兄探了路?他可又欠了我一遭。”
方應看發現全府的人都被悄無聲息地制住而冰冷的掌心開始冒汗,他看了一眼身邊伺候的人,對方悄無聲息地點頭離開了,坐在堂中的人并未阻止。
這并沒有讓方應看放松下來,恰恰相反,他的笑容越發勉強了:“關聖主竟悄無聲息到了汴京,您與義父是多年的朋友,也是在下的長輩,何必鬧出這番動靜來呢?讓這些下人也受了驚。”
“您對晚輩大概是有些誤會,您若有什麽不滿,大可以直言,晚輩一定敬聽教誨。”
晚風徐徐,月色清冷,燈火搖曳,華庭璀璨。
站在庭中的白衣青年面帶苦色,仿佛真是一個被父親長輩誤會了的好孩子,恭順謙和,不卑不亢。
他身後是沉沉的黑夜,身前是高堂玉軒,被人群簇擁着,确實尊貴榮華,氣度不凡。
顧绛想到在這侯府中的所見所聞,再看眼前人的堂皇樣貌,驀地笑出了聲:“好,裝也要裝到底,此時氣急敗壞,已然無濟于事,還辜負了良宵好景。”
“我今夜乘興而來,小侯爺切莫使我敗興而歸。”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