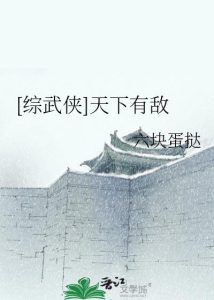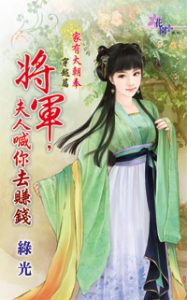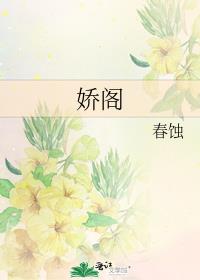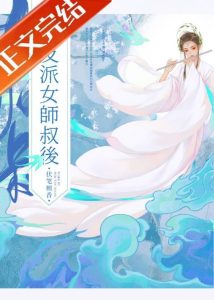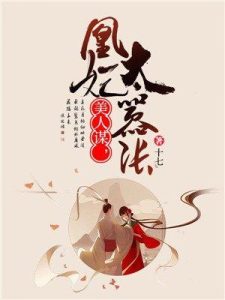道魔 11
武當山,自漢朝起,這裏就是尋仙求道的隐居之地,忽必烈将武當譽為“福地”。
一峰傲立萬山圍,半壁丹崖半翠微。真武當年修煉處,仙臺自在白雲飛。
在避諱皇帝之名,改玄武為真武之前,武當便以龜蛇之相作為玄武帝君的道場,武當武當,非真武不足以當之也,自唐代起,武當便是一座道教名山。
山上道觀不少,主殿是宋宣宗時建起的紫霄宮,至于後世所見的建築群大多興建于明代,那時的武當山因張三豐揚名天下,被明朝皇室尊奉,幾乎相當于皇室家廟,規模地位自然不是現在能比的。
這山中也有個“武當派”,可此“武當派”非彼“武當派”,只能算作如今正道的幾大門派之一。
若此世真有三豐道人在,以他道武結合、丹劍雙絕的境界,該是廣成子、呂純陽一樣的人物,在這個個人武力能夠定鼎天下的世界,魔門還能不能掌控朝政,都成問題了。
縱然沒有張真人坐鎮,如今的武當依舊是道門最大的門派,有武當派自身實力的原因,也有道門武力衰頹,各家傳承中斷的緣故,昔年的天師道、上清派、樓觀道、龍門派等道門大派,都在王朝興滅中去武向法,漸漸沒落。
尤其是宋末時,道門與佛門的一場争鬥,使得太清宮都被一場大火焚盡,道門自此再無道尊。
北宋末年,金門羽客林靈素入龍庭,雖然許多道門支脈覺得他行事過于大膽,但這位神仙道人開創神霄派,引徽宗入道,一度以道滅佛,确實是壓倒天下的人物,他将釋迦改為天尊,菩薩改為大士,羅漢改為尊者,和尚改為德士,要佛門之人從道教規範,留發戴冠執簡。
“他以慈航靜齋不落發為由,逼問天下佛門,想要将佛教并入道教中,幾乎逼得慈航靜齋上下剃的光頭,以表立場。所以,雖然道門中反對他幹涉朝政的不少,可依舊尊崇他為道尊,佩服他的武功修為和驚天手段。”
“可惜他确實行事太過,逼人太緊,惹來佛門之人的圍攻,那慈航靜齋的傳人更說動了本就好色的徽宗皇帝,使得林靈素不得不退去,兩教鬧得一度水火不容,道門落敗,損失極大,林靈素也成了道門最後一任道尊。”
蒙元皇室藏書庫中那些從兩宋流傳下來的道藏,絕大多數就是當年林靈素帶入宮中的,顧绛在那些書裏泡了十年,從浩如煙海的書卷中鑄就道心,說不得還得謝謝這位道尊的慷慨。
這些消息,是顧绛在武當山上混了一個月,從一些老道士口中得知的。
“不過佛門也沒讨到好處,南宋時密藏第一高手南下,與中土佛門争奪法脈,第九代慈航靜齋齋主雲想真與淨念禪院的虛玄二人齊出,雲想真劍勝法王,但他們三人歸去後,沒多久都圓寂了,那藏地的大和尚留下遺言,只要這兩家的傳人下山,藏地佛教就一定不能坐視,所以那兩家已多年不在江湖走動了,說到底,也是怕了那些喇嘛。”
“嘿嘿,他們當年兩個打一個,才擊退藏地的大和尚,難怪人家不服氣呢。”
老道士形容清矍,已有百餘歲年紀,說起兩宋舊事,滔滔不絕,化名明玉的道人捧着茶,饒有興致地聽他講古。
顧绛自己都沒想到,憐星這張臉在正道中竟如此好用,那些大大小小的道士見明玉道人有姑射之姿、氣質天然,便認定她是個和善女子,有道之士,對她很是親近熱絡。
明玉看出了老道人那股延續自兩宋的脾性,對慈航靜齋和淨念禪院意見不小,便笑盈盈道:“我曾聽人說,那慈航靜齋既不剃度,也不着僧衣,不念經文,不拜諸佛,修到極致時內蘊道胎,而不是佛胎琉璃相,我還以為她們和我一樣,是道門出身哩。”
她說話時神态天真,好像真是這麽覺得,老道士大笑道:“她們祖師號稱地尼,乃是淨念禪院之祖天僧的師妹,當然是佛門之人,只是那地尼與魔門邪帝謝眺有一段舊情,又因為融合道佛的觀念,和天僧異路,自己另創了慈航靜齋,她留下的傳承自然也是佛不佛、道不道,還和魔門掰扯不清的。”
明玉眸光流轉,心中有些納罕,嘴上便說出來:“這麽說來,慈航靜齋其實只是名分上歸屬佛門,她們的立派之本是地尼的理念,自成一家了?”
老道人睨了她一眼,笑道:“你這丫頭對佛道兩家的修為也不淺啊,怎麽,想去看看慈航靜齋的武功?”
明玉這段日子和武當山上的道士論道,故而紫霄宮上下都知曉她學問道法修為極深,兼修佛、儒兩家,有三教合一的跡象,但還沒有人見過她動手,只幾個老道士看出她幾分根底,讓底下的徒子徒孫莫要怠慢了這位道友。
老道人嘆道:“你天生靈性,小小年紀就修成道心圓滿,那些沒什麽眼力的小道士們見了你,便覺見‘道’,心生親近向往,便是老道我也不能免。若要以我私心來論,我是不希望你找上慈航靜齋的,以你的資質,就該安心修行,叩問天道,而不是牽扯進那一脈的麻煩裏去。”
道家講修身、無為、煉氣、長生,順其自然,追求人與道合、神游天地的忘情逍遙、和光同塵;而佛家講因緣、業力、生滅、正果,慈悲渡生,追求超脫因果循環,達到非生非死的清淨、寂滅。
此時的儒家正是理學盛行時,認為人欲是惡,是一切災難的起源,要規範自身、追求大同,就該摒棄人性中向別人求索的貪婪,而向天理去行,即“存天理、滅人欲”。
能夠貫通三家學說,鑄就道心,假以時日,必然是名震天下的人物,道門式微,若能出一個不世之人,重塑道門根基,便足以振奮、凝聚人心。
老道士是真的不希望她早早的和慈航靜齋扯上關系,哪怕去尋少林和淨念禪院呢?
明玉背手敲了敲自己身後的長劍道:“您放心,我對慈航靜齋的佛理不感興趣,她們的門人弟子大多不下山修行,一生居于山中,佛祖釋迦牟尼都需要在家國之災、萬般苦難中修行出菩提正果,似她們這樣除非道争和國争,從不出山,又能念幾分真經?閉目合十,就能問清淨至境?”
“我只是對《慈航劍典》有幾分興趣。”
聽老道士說慈航靜齋自漢代立派,千年間能入“劍心通明”境界的都屈指可數,更不要說飛升了,明玉頓時對慈航靜齋的興趣大減。
就這百年間,從令東來到傳鷹,再到蒙赤行和巴師八,就有四位破碎,或破碎虛空,或破碎金剛,而慈航靜齋身負聖地之名,千年能有多少天縱之才,居然一個飛升的都沒有,可見慈航靜齋的道路本身就有問題。
現在她只想看看《慈航劍典》的招數,地尼的武學根基既然與邪帝謝眺有關,那她們的武學或許對佛門、道門無所增益,卻和魔門息息相關。
不過,不急。
老道士輕撫長須,道:“也是,你既然出身曾經的關中劍派,雖然上清派的許多傳承都斷了,散入江湖中的支脈依舊有不少劍道高手,可惜我武當派以丹法和拳掌為主,劍法上除了《無量劍法》,沒什麽可以和你切磋讨教的。”
明玉卻笑道:“這些日子諸位同修待我極好,我自幼在山中清修,師父和姐姐離去後,就孤身一人,大道難行,武當派的師兄弟們要是對劍法有興趣,我可以教他們。”
老道人撫須的手一頓,正色道:“這是什麽話?你孤身一人,師門又沒有個确切的出身,若将劍法教給我武當,就是将傳承拱手相讓,傳出去,還道咱們欺負你無依無靠。”
明玉卻覺得他這些顧慮很沒意思:“這些日子,我聽您講了許多過去的事,佛道相争,都曾一度沒落,佛門依舊能複興,道門卻依舊沒落,私以為不僅僅是因為道門弟子下山修行、投身亂世,許多優秀的弟子早早喪命的原因,還有諸多法脈敝帚自珍,不肯交流互通、革陳出新、再創新天的緣故。”
“若集各家所學,創出一門入手簡單,修行深了可通大道的武功,卻願意将它流傳天下,以武興道,助天下百姓強身健體,只要有靈心道性之人,都能從中窺見道家之理,從而引入道門。”
“那時,何需一派一脈之名?又何愁道門衰頹?”
若在別的世界,這種影響也許不會這麽大,但這是武俠世界,是一個武林各派、黑白兩道能主宰王朝興亡的世界。
老道人深深望着明玉,良久才緩緩道:“這世上諸多直指大道的武學,都有自己的門檻,你所說的這種,悟性低的能強身健體,悟性高的能悟出道門至理的武功,便是諸位祖師都未能得出,若有人能創出這樣的武功,便足以名傳萬代,開山做祖。”
明玉微笑道:“這門武功倒也不是我所創的,只是我少年時,與一山中種地的老道士關系不錯,他見我習武練劍,就也拿了劍來與我對打,上清劍法以淩厲殺伐為主,講究一劍破萬法,諸劫燼滅,可那位老人以木枝為劍,往往後發先至,混元無相,無論我怎麽攻他弱點,都會被他化解,我便向他學了這門劍法,并一門拳法。”
她最初接觸這門武功,的确也是在武當山,山下的田地裏,幾個武當派的老道士耕田種菜,還是東方不敗的他和沖虛過招,見識了沖虛的武當絕學,那時他對這門武功的感觸并不深,哪怕是齊乘雲得道時,她的道基也是逍遙派的逍遙忘我,直到這個世界,她修行道心種魔,才真正開始回想這門後世流傳天下的絕學。
明玉撿起一根樹枝,在地上畫了一個圓,用曲線從中分開,兩邊各畫一個小圓。
老道人當然認識這幅圖:“太極。相傳此圖流傳自上古,與先天八卦同生,是陰陽相濟之理,因其中道理無窮,卻不着一字,又被譽為‘無字天書’,道門中最得此道的,還是宋時的陳抟老祖,看來你說的那位老人,是陳抟一脈。”
明玉指着太極圖道:“是,這是我博覽易理,探索古今天地之學後,最終明白的,即大道至簡。道門曾有一樣至寶,名為天地心三佩,天地兩佩是兩極的力量,生與死、清與濁、陰與陽,兩者看似泾渭分明,終究在心佩上融為一個整體,從而洞開仙門,天師孫恩因此飛升而去。”
道心種魔其實也是這個道理,道心為陰極,魔種為陽極,道心種魔所追求的,從來不是以魔勝道,而是陰陽相濟,達到平衡的境界,最終将兩者融為一體。
真正的智慧,是不被世界的武學等級所限制的。
張三豐将太極之理化入武學,晚年所成的太極拳、劍,其中的根本道理,放在這個世界,依舊是一條通天大道。
将道魔代入陰陽兩極,她所創的這門《道心種魔》與太極武學雖然練法完全不一樣,但在武學道理上,堪稱殊途同歸。
這才是為什麽,她期盼能與三豐道人一會,因為她能感覺到,自己走的路,和張三豐的武道,也相當于天道這個太極上的陰陽兩魚,陽者活躍,陰者沉恒,我為陽極,他為陰極,一魔一道,若能與三豐道人交手,她一定能再上一層樓!
結果這個世界居然沒有張三豐。
大失所望的明玉來到武當山,除了想要混進正道,看一看他們的所學,也是想要在沒有條件的情況下創造條件。
她能勒令魔門勤習武學,每二十年就去刮一次他們的皮,也能以天下道門之人為根基,将張三豐的武學理念傳播天下,等着從中走出一個“張三豐”來。
想到這裏,明玉笑得越發溫婉柔和起來,一雙明眸如星,用道心壓制住蠢蠢欲動的魔種,對老道人說:“我願意将那位三豐道人教我的武功教給各位同修,不知諸位是否願意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