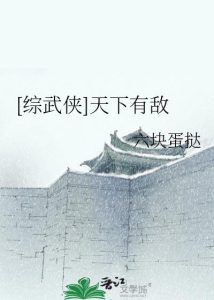據慕瑾所知,今夜是不該輪到若荷守夜的。
若荷入了門之後,便朝着唐天戈和慕瑾輕渡了兩步。這個時候,慕瑾才發覺若荷的手上拿着一個不大的物件,似乎是一個原木制作的盒子,很是精致。
聽後了慕瑾的問話,她輕輕的将雙手中捧至的木盒擡起,小心翼翼道:“奴婢不該打攪陛下和娘娘,只是方才郭太醫囑咐了,這香是安胎的良方,務必讓娘娘安睡的時候點着。”
安胎的香?慕瑾微微蹙眉,心下有些許的疑惑。以燃香安胎之法,她是從未見人用過的。 然而唐天戈确是不以為然,他見了慕瑾一臉困惑的樣子,索性便開口解釋道:“在這南越王宮,歷代便是實行以熏香安胎的。這可供安胎的熏香皆是由上好的安胎藥材制成,味道與普通的熏香無誤,而
安胎的效果确是可與直服中藥匹及。”
他言完此語,看着慕瑾臉上恍悟的表情,擡眸望向了站在一側的若荷:“這藥香可是郭太醫開的?”
若荷聞言之後輕輕的點了點頭,極其淡然開口補充道:“回陛下,正是。郭太醫說,這藥香是由藿香和黃芩制成,安胎之效是極好的,正好适合娘娘這氣虛脾涼的身子。”
見若荷如此言說,慕瑾也便安下了心來,心下領會之後言說道:“既然是郭太醫特意囑咐的,那你便将這屋中的沉香掐了,燃上這藿香。”
慕瑾言說完後,擡眼望向了身後的唐天戈,唐天戈雖然并未言說,卻是心下默許了慕瑾的吩咐。
若荷見狀,忙垂眸應聲道:“是。”言罷之後便朝着那香爐的方向走去了。
她輕輕的将那裝有藥香的木盒打開,裏面塞有百餘根藥香,顯得鼓鼓囊囊的有些冒尖。若荷便将從那表面的一層藥香中輕輕的抽出一根來,緩緩的燃上。
看着那燃起的熏煙在眼前暈染開來,若荷有一瞬間的愣神,可是馬上便恢複了神志,擡起手來将那打開的盒蓋複原合上了。
做好這一切之後,若荷又将那盒子塞到了原先香盒的旁邊,方才回過眸子來,望向床榻上的兩個人。 在她燃香的過程之中,唐天戈和慕瑾并未看着她,而是依偎在一起,不知說着什麽話。若荷悄然的松了口氣,緩緩的走至了離兩人七尺餘的地前,彎曲着身子請安道:“陛下,娘娘,那奴婢便先行告退
了。”
她擡眼看着不遠處的二人,見唐天戈緩緩的朝她擺了擺手,若荷便将頭垂下,緩然的告退了。
月亮蕩漾在雲朵之上,透出了些許的光輝傾灑在這賢靈宮的寝殿之中。
“朕方才,說到哪了?”唐天戈輕言道,剛剛只顧着想那藥香之事,就忘記了兩人交談到了何處。
而慕瑾自然是記得自己方才應允的話的,她有些羞愧,亦是覺得有些尴尬,便并未将那句話再次點名。
而唐天戈見慕瑾如此嬌羞的模樣,卻是又突然憶起了她剛才的話的。
心下有幾分的悸動,更多的則是欣喜:“阿瑾,可是答應了朕,同朕一塊去看朕的父母?”
慕瑾有些難再啓齒,便未再應允。唐天戈卻是溫柔的攬過了她的肩頭,小心翼翼的言之:“謝謝你,阿瑾。”
這是只有他們二人能聽到的聲響,傳遞至耳膜便只剩下了一絲氣音。而唐天戈呼出的熱氣卻傾灑在她的臉頰旁,讓她切時的感受到了這一切的真實性。
她小幅度的向後退了退,并不是畏懼眼前的唐天戈,只是身在這種感覺中稍稍有些不自然。
唐天戈也感受到了慕瑾的動作,卻是只當以為她在擔心祭祖之時,便順着她後退的幅度緩然上前移了一寸。 唐天戈凝望着慕瑾澄澈的眼眸,言語溫柔道:“阿瑾,你不用擔心,朕的母親還在世的時候,經常同朕講,她同父皇入宮的這些年,雖然寂寞是多于相守的,可是她并不後悔。她告訴了朕,一定要尋得
一個此生摯愛的人,否則這一生都是茍且。而朕這一生摯愛的人便是你,所以,母親大人一定會喜歡你的。”
他稍些頓了頓,将臂彎中的慕瑾摟的更緊:“至于父皇……阿瑾你也不要擔心。父皇當年瞞着所有人将母親的靈柩葬入皇陵,他定是明白何為摯愛,何為珍惜的。母親基于父皇,便是阿瑾基于朕。”
“父皇亦是定能理解,朕對阿瑾的真心的。”他言完這最後一句話,輕聲的嘆了口氣,心下已然是做好了決定。
而慕瑾聽着唐天戈的言辭,心下亦是有些許的情緒在翻湧。
她不止一次聽唐天戈談論起他的母親,亦就是前朝的那位德妃娘娘。唐天戈從來不喚德妃娘娘為母妃,反倒是像尋常人家一樣,喚她為母親。
或許是因為唐天戈幼年童稚之時曾于宮外生活養下了如此的習慣,亦或者,是因為在唐天戈的心中,母親從來就不是南越先皇的妃氏,而是他一生唯一的伴侶。
這想着想着,慕瑾不由的便聯想到了自己的父母。同樣是深陷皇宮貴族,同樣是妻室早夭。
不同的是,自己的母後是父皇慕言的結發妻子,陪伴着他打下天下,登上皇位。而結局,卻是在大好年華香消玉殒。
父皇亦是母後心中的唯一,而母後卻不是父皇唯一的皇後。 母後病逝之時,父皇以皇後之禮厚葬于她,卻又在不出三月便冊立了華氏為皇後。從那以後,母後的碑位前便是常年空虛,只有她和慕珏二人會在節日與忌辰間前去探望。她的父皇,是一次都不曾去
看過母後的。
慕瑾不禁的勾起了一抹苦笑,她擡眸望着唐天戈噙着笑意的面孔,心下湧生了些許的傷懷。
唐天戈心中那種珍視着的愛情,當真會在這皇宮中顯現? 一廂情願确是簡單,而似南越先皇與德妃娘娘這種兩相珍重的感情,卻是着實不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