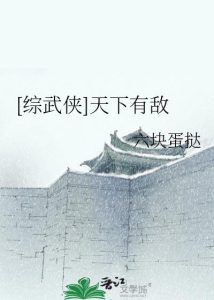迷天 17
楚相玉第三次行刺徽宗,被諸葛正我擒下入獄時,顧绛正帶着兩個孩子在陝晉之地觀看黃河壺口瀑布,他既然答應過要帶他們去看大河,那當然要看天下最雄壯的景觀。
煙從水底升,船在旱地行。未霁彩虹舞,晴空雨濛濛。旱天鳴驚雷,危岩挂冰峰。海立千山飛,十裏走蛟龍。
數百米寬的大河要在陡收為數十米的壺口斷崖沖落,千裏黃河一壺收,水落層岩,當真石破天驚。
九月正是黃河汛期,大河水奔騰咆哮,穿過龍洞就能見到上方瀑布,升騰的霧氣不知是水還是沙,只覺陣陣轟鳴,震耳欲聾。
溫純一開始還提着裙子,害怕被淋濕,後來發現在這大河邊行走,避免不了要被淋了,幹脆也不管裙子和鞋襪,開心地在石面流水間蹦蹦跳跳的向前,她今年八歲了,雖然還沒有習武,但身體素質和普通八歲女孩已經沒什麽區別,看着端莊文靜,其實頗為好動。
比起溫純,盛崖餘就安靜許多了,他跟在顧绛身邊一步步走過來,腳步踩得很穩,他有三位名師教導,諸葛正我身為“文林之仙”,雖以武名動天下,但在朝堂上,他還是以文進位的,盛崖餘的詩書都是他所教,而機關、陣法等技法則學自許笑一。
顧绛回到汴京時才教他武功,畢竟武學的基礎要靠練,只要在諸葛正我等人的看顧下,不教他練錯,靠他自己的自律勤苦,根基總能打好的。
基礎打好之後,他才帶着他們出門。
顧绛指着前方瀑布道:“武學之道原本就來自天地自然之間,只教一招一式、如何運氣用招的不過是平庸武師,真正的傳道之師,是要告訴你道在哪裏,你該如何去求的,哪怕你還未到體會其中真意的境界,但只要見過真意,便能尋跡而去,終有一天超越前人所抵達的境界。”
求道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這條路上的人越多,能為人所認知了解的路途才會越開闊,與其說他們在傳授自己所得的道理,不如說他們在培養更多同行者,并真心期待着有人能超過自己。
他說完,一手抓住盛崖餘的手臂,一手撈起了溫純,縱身躍下石岸,在溫純驚聲歡笑中,在滾滾的河水之上,逆流而行。
在這個武道昌明的世界,武功練到極致會有大多的威力?
關七能夠在體察天心時看見過去未來,甚至隐隐窺見一個人的命運結局,他是真正橫亘一世的萬人敵,即無論多少人圍攻,也絕殺不了他的存在。
所有人都只見他不敗,但終究無法衡量他的武功有多高。
他也能靠自己的力量引動天象,讓晴天落雷嗎?
他也能以一人之力抗衡整個江湖嗎?
今日在這黃河壺口之下,兩個十歲、八歲的孩子,見到了人力在這個世界的極限。
白衣男子伫立河上,翻騰的水汽不能沾染半分,他明明已經年過而立,乍一看也的确面帶風霜,可當他睜眼看過來時,依舊像個十七八歲的風流少年。
他把穿着翠綠衣衫的小姑娘放到自己另一邊的肩背上,然後緩緩擡起了手,他手中沒有劍,反而是腰間佩着一把刀,但不應寂靜得很,風中卻傳來了一聲铮鳴,明明十分細微的聲音,卻壓下了悍然的波濤聲。
有那麽一瞬,世間所有聲音都消失了,風聲、水聲、鳥雀的啼聲,甚至是三人呼吸的聲音都消失了。
天地靜默中只有那一聲劍鳴。
然後壯闊天下的大河瀑布被攔腰截斷。
顧绛踏着斷流下裸露出的岩石,在河水再度傾瀉而下前飄飄然落到了高崖岸上。
溫純抱着父親,她瞪大了眼睛望着已經恢複原樣的瀑布,吸聲問道:“阿爹,武功要怎麽練,才能到你這麽厲害?”
其實以溫純的天賦,她就算練到一百歲也抵達不了顧绛的境界,她天生經脈細弱,雖然能運使《先天罡氣》或者《破氣神功》這樣的武功,但它們都只在出招時聚氣,收招又散去,好用,卻不夠深厚,沒有深厚的基礎,縱然也能有所成就,但絕不可能練成顧绛他們這些人的武功。
這是天資的限制,就像有的人生來就聰明,而有的人生來就智商不高一樣。
但顧绛沒有打擊她的意思,相反,刻意在他們面前施展劍氣,就是為了讓他們看到江湖上最頂尖的高手能有多高:“和讀書、學醫一樣,要刻苦、堅持,有足夠高的悟性和足夠好的根骨。”
溫純聽到“根骨”,神色黯淡下來,盛崖餘雖然之前也受過傷,但是傷養好後續上了經絡,雖然腿還是有點毛病,但已經完全不影響他習武了,他握着師父的手,看向師妹說道:“就如讀書一樣,很多人畢生也做不到阿純這樣過目不忘,所以天下也只有一個關七聖。”
關木旦忙于事業,其實對女兒的陪伴并不多,這些年蘇夢枕也忙碌起來,所以反倒是一度傷病不起的盛崖餘和溫純更熟悉,他因為家仇性子有些冷僻,但骨子裏十分細致,看得出溫純其實一直很仰慕自己的父親——迷天盟中沒有人不仰慕七聖主,何況是他的親生女兒,他們告訴過溫純,她的身世來歷,但正因如此,她心中一直都很介意自己的姓氏。
在這個時代的文化背景中,姓氏的傳承往往代表了“繼承”和“認可”,溫純自出生從未見過自己的母親溫小白,她和溫小白沒有任何感情,甚至并不喜歡溫小白的一些處事方式,尤其是自己這個素未謀面的母親因為一時的任性,害得父親在練功的關鍵時刻走火入魔,至今還在被舊傷困擾。
父親雖然很少陪伴自己,但他對自己極好,從不以世俗規矩限制她,還教她讀書習字、武功兵法、經世學問,要知道,哪怕是一些書香門第、王公貴族,他們教導女兒時也讓她們讀詩書,但出發點都是為了讓她們以後能更好地經營家庭、輔佐丈夫、教育孩子,甚至幫助家族、傳承師門,而不是希望于她們學有所成,能做出一番自己的事業。
哪怕抛開這些,就論她的吃穿用度,迷天盟所有人的尊敬愛護,包括那些叔叔伯伯的照顧,本質都源于她的父親。
但溫純不僅長得完全像溫小白,體質也不像關七,連姓氏都繼承了母親,敏感多思如溫純,多少會覺得失落。
這才是她會介意那些人說她不如蘇夢枕和雷媚的根源,因為在絕大多數江湖人眼裏,她都稱得上是“子不類父”了。
她沒有把這些心思說出來,旁人也不會想到這麽小的姑娘就會想這麽多,只有盛崖餘看出了一些。
顧绛沒有那麽細膩的心思,他只是覺得溫純因為自身的體質不佳一直有些放不下,長此以往,會成為心結,就像盛崖餘的仇恨,它們可能會成為一時的動力,但長久下去,就會成為障礙,所以顧绛才要帶他們出門。
當然,他本就要到陝晉之地走一趟,因為這裏不僅有大河,還有綿延西北多年的關中群寇。
關中流寇和江南盜匪有着很大不同。
江南的盜匪大多圍繞着土地誕生,因為受不了官員的搜刮、地主的欺壓而聚衆起事,他們的追求是田地錢糧,所以只要他們占據城池,以北宋的器械和精銳軍隊的實力,這層出不窮的農民起義就會被一直鎮壓、招安、填充入軍隊。
而陝地的流寇多是邊軍出身,因為北宋和西夏的戰事,以及宋朝軍中的惡劣風氣,早在太宗年間就有關中“叛卒”劉渥聚衆千人生事,其人骁勇無敵,稱自己“草間求活,視死如鴻毛”;仁宗年間的張海也是逃軍,其人馳騁五六路二三十州,數千裏內,如入無人之境,自陝西到江淮,殺官入縣,開庫濟民,運動作戰,在民間聲名極好,反倒是宋庭派出去鎮壓的官軍燒殺搶掠,殺良冒功,連宋庭自己都承認“官兵過處,勝于盜賊”,直到哲宗年間都有朝臣談之色變,稱“張海橫行半天下”。
一件事情如果反複發生,那就說明不是人導致的偶然問題,而是這個地方有問題,這裏的政策有問題。常年對西夏作戰卻不能徹底解決戰事的拉鋸,不停征調民役,好好的農民都拉來黥面配軍,動辄打罵,配合陝西一代本就困難的經濟狀況,以及爛透了的腐敗問題,出逃的軍士在軍中得不到重用,自己領人造反卻能鬧出偌大動靜來,不得不說是一種諷刺。
顧绛如果想經營北方,和西軍沒什麽好說的,但關中群寇倒是可以往來。
——————
顧绛帶着兩個孩子出入綠林,這是他們第一次走出“家門”,看到這個國家的弊病沉疴,以及在這片土地上艱難求活的百姓。
盛崖餘本以為師父帶自己和阿純來到匪窩山寨這些地方,已經很過了,關七這麽做,是因為他有這個本事在群狼中保護他們;但他萬萬沒想到會在這裏看見一群和自己差不多大的男孩做流寇打扮,互相用木棍劈砍演練,招招狠辣。
關中龍頭咬着幹果,笑道:“小公子十分訝異?你覺得咱們這些人是為什麽嘯聚山林,到處游走的?為了打家劫舍求富貴嗎?”
“咱們這兒大多數人,一開始只是想活下來罷了。”
“那幾個小孩有的是跟着爹娘一起來的,有的是爹被拉去充軍,娘維持不了家中生計,自己跑出來跟着咱們,就圖一口飯吃,我答應給他們飯吃,他們就跟着咱們殺人。”
關中龍頭嘿了一聲道:“咱們這些人和小公子你們這樣的矜貴人物不一樣,一條命輕賤得很,從不奢望什麽大富大貴,官家招安當官,咱們就是從軍營裏出來的,還能不知道當官是怎麽回事嗎?說到底,誰能讓咱們活得像個人,咱們就跟着誰過下去罷了。”
顧绛擡眼道:“他們跟着你們可以活一時,只怕也活不了太久,那些邊軍應付完西夏,就會抽手回來對付你們,你這樣軍營裏出來的也應該很清楚,你們可以及時游走,無懼剿殺,可他們殺人,不問老弱婦孺。”
關中龍頭面帶厭惡地罵了一聲,但他也沒有否認,畢竟這是三國邊境上所有軍隊一致的風格,匪過如梳,兵過如篦,從來如此,反而是軍紀嚴明、對百姓秋毫不犯的軍隊才稀奇。
顧绛要的就是這樣的兵,沒有紀律的軍隊不能運使如意,沒有思想的軍隊更是一盤散沙。他們若是僅僅為了活着當兵,那這些人自然會去追求讓自己活得更好的東西:財富、權力,從而去劫掠百姓,當情勢不對時,以保住自己的性命為首要,在戰場上做逃兵。
西夏、遼國、金國,包括多年後才崛起的蒙古都以騎兵縱橫天下,游牧民族弓馬娴熟,輕騎兵配合重騎兵在戰場上所向披靡,北宋的騎兵比不上他們,就轉而練成了重甲步兵,以重兵器專破馬腿,但兩軍在戰場上交鋒時,面對正面沖過來的重騎兵,必須有不畏死的勇氣才能維持住陣線,并沖到馬下砍斷奔馳中駿馬的腿。
這才是後來南宋名将能破金軍的緣故。
但武俠世界和普通世界不一樣,在這個世界,有一種東西可以更好地破解騎兵陣營——霹靂堂的火藥。
若是霹靂堂雷家的弟子運用起火藥來,當然得心應手,但普通士兵就不一樣了,這東西還是有不穩定性的,必須是熟手才能靈活使用。
顧绛看着那些少年人道:“來之前我就與閣下說過,你們有你們的作風,我有我的規矩。比如說這些孩子,我不是不能接受,但我不會讓一群不滿十六歲的娃娃去送死,你承諾給他們一口飯吃,可以。我不光給他們吃飯,還要讓他們識字、習武,到時候他們願意繼續跟着走的,就和我們一起出關,不願意的,就去中原為我做別的事,直到還完我花在他們身上的精力。”
迎着關中龍頭幽幽的雙眼,顧绛道:“而我對你們的要求,只有一點,我不要懦夫。”
龍頭忽大笑道:“我等草間求活,視死如鴻毛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