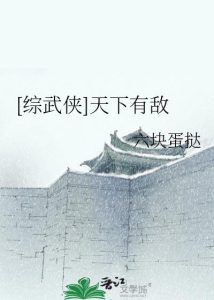入了夜,白芷推開窗,徐徐夜風吹來,竟也有些涼,白芷披了件繡着仙鶴的藍海松茶色鬥篷出客棧,客棧裏還有三兩食客正在用飯,只瞧見她的一個背影,鬥篷上的仙鶴栩栩如生,鶴頭一直延伸到兜帽處,仿佛一陣風吹來,就能振翅飛翔一般,十分逼真。
她穿過水杉林,再次來到沙灘,想看看貓哥這可有收獲。
攤位旁都掌了燈籠,棧橋上依然有鼎天宮弟子把守,有些許鬼火緩緩而來,鼎天宮竟也放行了,看來此仙市也是來者不拒。
夜晚降臨,貓哥白天睡夠了,精神抖擻的盯着緩緩前行的鬼火們,也點了盞小燈,豆大的燭火有法術做保護,不會被風吹滅,剛巧籠罩了他鋪好的白布。
白芷來到此處,坐在燭光照不到的陰暗處,将整個身子攏在鬥篷裏。
“收獲還不錯。”貓哥說。
趁着夜色,貓哥将收來的東西都交給了白芷,白芷粗略看了一眼,還收了三塊建木千年皮,收入到乾坤袋裏,道了謝,又問:“鬼界怎麽也有人來此地。”
衆所周知,鬼界平日常閉大門,進出不易,極少參與六界中事,算是比較中立的一界了。
貓哥舔着爪子,表示對此并不清楚。
夜空中一顆流星飛快掠過,白芷仰望天際,感受着微風吹來,而後輕輕嘆了口氣。
“這位姑娘面露憂色,定是有什麽心事,不如一吐為快,疏解心結。”從黑暗中飄來一盞幽藍鬼火,站定在陰暗裏,保持了一定距離。
白芷眯眼看去,嘴角露出個有些陰森的笑:“都做鬼了,管的還那麽寬,哪涼快哪待着去。”她言語之中無絲毫客套,只希望對方勿擾。
白色攤布上緩緩出現了一些東西,貓哥忙去看,發現都是他收的東西:“是陷山古玉髓!”說罷,他查了查,補充了句:“正好二十個。”
生意上門,不該有推拒的理由,只是白芷現在心情不大好,心裏存了事兒,無心理會,便道:“貓哥,你招呼一下。”言罷,白芷就要離開,幽藍鬼火已經化作一名玄衣公子,攔住了她的腳步。
“姑娘,請留步!”他作了一揖,又自我介紹:“敝人壇言,今日聽聞此處收陷山古玉髓,敝人這些陷山古玉髓并不需要易物,而是想求姑娘幫個忙。”
“你找錯人了,這個攤位的主人是這只貓。”白芷并不領情。
壇言笑了笑,說道:“我在陰暗處觀察了它大半天,他并不是這個攤位的主人。”
貓哥炸毛:“你竟然偷窺我,而且還偷窺了大半天!?”
白芷被貓哥逗笑了,攤攤手說:“好吧,就算我是這個攤位的主人,可我并不想以‘幫忙’作為交易,你現在明白了嗎?”白芷轉身繼續走。
“姑娘,好歹當年我也是幫了你一個大忙,你怎可翻臉不認人?”壇言又化成鬼火緊追而上,在她身後說。
白芷權當沒聽見,繼續走自己的。
壇言锲而不舍:“承淺當年私闖鬼界,私自覆在蘇鏡身上的事,是我幫忙瞞下來的!”
白芷神色微動,腳步卻沒停,已經走入水杉林了。
過去時,過去事,白芷大可不承認。
“白芷真神,我知道樓西岳前世因果,後世轉生,神上就不想再續前緣嗎?!”壇言抛出了最大的誘餌。
白芷站定腳步,撼天魔氣忽然爆發,她轉身時已經出手掐住了那顆幽藍鬼火,眼眸泛紅,兜帽随着她猛烈的動作而滑落,她的發被風吹的翻飛,邪風自她身上擴散開來,方才還晴空萬裏明月當空的夜覆滿了烏雲,月色猶如她的眼眸,也泛起了微紅。
那顆幽藍鬼火漸漸顯露身形,壇言被她掐着脖子推壓在水杉樹上,他并未露出膽怯,而是掙紮說道:“我不是在威脅你,只是想請你幫忙。”
林中鳥獸四散奔逃,一時間水杉林裏的活物只剩下他們倆,白芷露出個陰森恐怖的笑,看的壇言寒顫,她極其平靜的說:“樓西岳已經死了,不管是前世,還是後世,都與我再無瓜葛。”
壇言詫然,不可思議的看着白芷,沒想到她竟是這樣想的!
“步秋塵的那句話要送給你才對……”白芷冷冷說,再次加深了力氣,似想折磨壇言。
“什麽?”壇言下意識的回問。
“你知道的太多了。”白芷冷冷說,手上一用力,那鬼火被她捏了個稀碎,猶如岩漿自她手掌心緩緩流下,滴落在地,發出滋啦滋啦的聲音。
她取了條手絹,厭惡的擦了擦手上殘留的幽火,最後扔了手絹,冷冷說道:“就當用那二十枚陷山古玉髓換你一條命吧,你賺了。”白芷邊說邊笑,有些瘆人,她将兜帽又重新戴上,向客棧方向而去。
樹林恢複寂靜,地上的幽藍火苗漸漸化成穿着玄衣的壇言,他的胸口被白芷掏出了一個血洞,即便是鬼,壇言也不想自己缺些零件兒,他查看了下自己的傷勢,發現并沒缺少什麽,放下了心。
壇言咳了幾聲,未曾想外表谪仙一般的白芷真神竟然下手如此狠絕乖戾,他這樣冒失的前來談條件,确實有失計謀。
可不管怎樣,小命卻是保住了。
呵,壇言苦笑。
穿梭人群的風帶走了燥熱,天空中陰雲交替,漸漸黑雲翻墨,雷聲千嶂落,雨色萬峰來。仙山頂峰的鼎天宮漸漸燃起了燈,締虛殿前,檐下暴雨如簾,一名眉目俊秀的青年與一耄耋老翁立于廊下觀雨。
老者掐指微算,一絲絲驚訝流露出來。
青年擡手接着檐下雨,雨水滲過指縫,流落在地,青年目光注視着自己的手,不急不緩的問:“如何,掌門?”
老者正是鼎天宮掌門李茂歸,李茂歸愁緒滿目,搖搖頭:“這劈天之雨異于天相,應當是有什麽東西混了進來。”
“什麽東西能在步秋塵真神眼皮子底下造次,當真活膩了不成?”青年神情戲谑,似乎并不将新晉真神步秋塵放在眼裏,是在說反話。
老者察覺到他的意思,勸道:“許溫,不是我說你,小心着些,你這脾性太容易得罪人了。”
青年正是鼎天宮副掌門許溫。
碧蘿葉被雨水砸的顫抖不止,許溫的心卻波瀾不驚,只望着漫天山雨說:“那妖物怕是奔着鼎天宮而來,派些得力弟子去山腰和沙灘尋覓一下吧。”
李茂歸一捋白須:“已經派弟子去了。”
山林之中,一席鼎天宮弟子穿梭其中,這些弟子偏不行正道,而是找些僻靜泥濘山路來走,其中為首的一名女子手持一小巧玲珑的燈籠,燈籠內無火光,而是有塊核桃大小的靈石,靈石散發出的薄光随着她的腳步而漸漸閃亮,直至刺目。
“大師姐,應當就是這附近了!”一名弟子道。
這位大師姐将燈籠左右試探着移動,向左時光芒有所減弱,向右時光芒增強,大師姐指了指右邊,警醒大家:“都小心着些,師父交待過,此物不凡。”
大師姐帶領諸人向右方尋去,天色如墨,又有樹林遮擋,連近處看的也并不真切。
“啊!”有人忽然驚叫。
衆人立刻圍了過去。
一名男弟子腳下被絆了一下,這才發現這裏躺着一人。
大師姐上前去,燈籠的光芒已經無法令人逼視,大師姐将燈籠裏的靈石取出裝入乾坤袋裏,嘆了口氣說道:“就是他了。”說罷,又給人遞了個眼色,那人上前探了鼻息,搖搖頭。
衆人皆嘆口氣,原來已經斷氣了。
“先帶回師父那裏去,請他老人家定奪吧。”大師姐說。
一名身材魁梧的弟子将人背上了寬闊的脊背,衆人趕回鼎天宮時,已經午夜了。
掌門李茂歸早已睡了,聽到有人來報,又整裝出來處理此事。
入了正殿,發現擔架上躺着一名男子,走進之後方才發現那人胸口被人掏出了個洞,他臉色浮白,唇色全無,好似已經死很久了。
“封山,給我抓住這食人心肺的兇手!”李茂歸氣的發抖,敢在鼎天宮行兇,手段如此惡劣殘忍,簡直是挑釁!
李茂歸令下,座下大弟子得令後迅速去安排了,不消片刻的工夫,先是沙灘棧橋處的弟子将棧橋撤下,而後仙島在一陣劇顫之中緩緩離岸,山搖地動,萬木簌簌,猶如地震。
衆人都已察覺到此等異樣,紛紛冒雨外出查看。
白芷也在這陣顫抖中醒來,推門來到客棧廳中才發現早已聚集衆人,議論紛紛。
這時客棧外跑來一人,是客棧的掌櫃,掌櫃張開雙臂向下壓,大喊道:“大家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不消片刻靜了,都等着掌櫃說話。
掌櫃神情緊張,大聲說道:“各位客官,方才山上弟子下達了掌門人的命令,說是要封山,此刻仙山已經遠離岸邊了。”
“為何要封山?!”
“是啊!”
“發生何事了?”
衆人向掌櫃發問。
白芷穿着一席淡青色襦裙,肩上随意披着件月白底子繡着秋海棠的褙子,頭上烏雲微堕,衣下肌膚猶如凝脂潤玉,透骨生香,她靠着紅漆柱子瞧着樓下,雙臂環抱在胸前,神情泰然不見絲毫緊張與急切。
于她來說,離岸又如何,縱然是仙山布下結界,她大可破界離去,所以對封山一說并不在意。
“說是有人被妖魔食了心肺而死,座上大怒,故而封山緝拿元兇。”客棧老板回答道,一時間聲音又暴漲,白芷掏了掏耳朵,想回屋繼續睡覺,剛轉身準備離開,卻聽到有一女子發聲:“那把下三界的人留下就好了,我們上三界的貴客,大可放行。”
此言引得衆人目光集中向她,那女子似乎也意識到了什麽,反譏道:“看什麽看?難道我說錯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