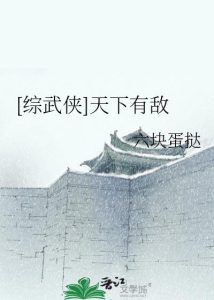見了若荷眉眼之間的慌亂,若蘭便同她解釋道:“這香既然有安神的功效,燃着自然是好的,讓它在這邊燃一會,待姐姐晚上回來睡的時候,也是助于減輕姐姐的頭痛的。” “不行。”若荷卻是在剎時厲聲的反對道,她頓了頓,似是也意識到了對妹妹的态度有些差,便繼續補充道:“你我二人都不在這偏房中,這熏香燃着……着實是不安全的,待到晚些時候,姐姐回來了再
點吧。”
若荷如此說着,若蘭心下便也了然了姐姐的顧慮,忙上前拽住了若荷的衣袖,緩言道:“是若蘭思慮不周了,姐姐不要生氣了。”
若荷凝望着眼前的若蘭,将眉眼之間的傷懷之情如數都壓制了下去:“沒事的,若蘭,是姐姐剛才反應太過激了。”
她頓了頓之後,輕聲的嘆了一口氣:“若蘭,你現在便去大殿門口候着吧,萬一陛下和娘娘有所吩咐,你我都不在的話是要被怪罪的。”
若蘭點了點頭,心下還在剛犯錯的忏悔之中,亦是未再問若荷為何要留于此處便輕渡着步子出了這偏房的門。
若荷看着若蘭消失在門口的身影,當這偏房的門完全合上的那一刻,她方才松了一口氣。
她輕輕的擡起了手臂,将那方才燃着的紫蘇香抽了出來,放置在了一旁放香的盒子裏。做完這一切之後,她又将那盒子用蓋子封住,輕渡着步子至了床榻邊,将那盒子輕輕的放置在了床下。
若荷輕緩的嘆了一口氣,慶幸着還好自己發覺的早。
父母将若蘭托付給自己,自己便應當保護好她,不讓她受到分毫的傷害。剩下的事情,不論是計謀還是複仇,都是她若荷自己一個人的事情,與若蘭毫無關聯。
如此想着,若荷堅定了神色,輕渡着步子出了這偏房。她知道做了如此的決定便回不去了,可依舊是下了決心前去太醫院。
當若荷抵達太醫院之時,太陽正在日頭上,曬得她靈臺有些發暈。
守門的侍衛見了她皆是微微蹙眉,用手中的利棍将其攔下道:“大膽奴婢,可知道這是什麽地方。” 若荷卻是不慌不忙的彎下了身子,緩然請示道:“奴婢是賢靈宮淑妃娘娘的貼身侍女,特命我家娘娘之名,來找郭太醫要一個安胎的方子,不知郭太醫可在院中?可否勞煩兩位,幫奴婢進去禀報一聲。
”
兩名侍衛聽聞了若荷的話面面相窺,要知道,如今這慕淑妃的名諱是多少人閉口不言的忌諱。
這宮中誰人不知,那個原先的淩國公主,母憑子貴做了淑妃,受盡了陛下的恩寵。
無論是她慕淑妃還是她肚子中的孩子,他們二人都是着實得罪不起的。
現如今,這名婢女奉着慕淑妃的命令,打着為皇子尋安胎方子的名號,他倆就算有幾個腦袋,亦是不敢得罪于她的。
于是二人便慌忙的将手中的利棍收了起來,陪着笑臉道:“原來是賢靈宮的人,小的剛剛失禮了,還請見諒。”
另一名侍衛見狀也趕忙彎曲了身子,緩道:“既然是慕淑妃的命令,那便是有關皇子的大事,爾等是絕對不能怠慢了。此時便不需要禀報了,郭太醫正在裏面調制着方子,你進去便是了。”
未曾想到這二人如此的爽快,若荷躊躇了片刻,微抿着雙唇言之:“那奴婢,便在此謝過兩位了。”
言完此語,她便在兩位侍衛的眼前,緩緩的邁上了這太醫院的臺階。
這太醫院着實是比外面看起來要大的,院之中充滿了草藥的香味,讓若荷有些許的留戀。可是她依舊沒有停留,依舊是極快的尋着那郭太醫的身影。
只是這太醫院之大,她竟一時未得尋見。
“姑娘,你在這作何?”身後有男子正在喚着她,若荷輕輕的回眸,便見着了眼前的人。
眼前是一個不過弱冠之年的男子,身穿着的卻是宮中太醫的宮服,想來應該是這太醫院的學徒吧。
若荷如實想着,便也請開口詢問了。
“哦,奴婢是賢靈宮淑妃娘娘的侍女,來這裏尋一下常給我家娘娘診治的郭太醫。”
那年輕的太醫聽聞之後,颔首點了點頭,回應道:“來找師傅啊,師傅他此時正在挑選中藥呢,你先跟我來吧。”
若荷聽了這名太醫的話,便點了點頭,跟随着他的腳步前去了。 這長廊甚是長,而因為此時衆多太醫都在大院之中,四處無人便顯得分外靜谧。那名太醫也似是覺得氣氛有些尴尬,方開口道:“小臣名喚初祎,郭姓,你方才言中的郭太醫便是小臣的叔父。我聽你剛
說,你是賢靈宮慕淑妃宮中的人?”
若荷聞言輕緩的點了點頭,還未曾接話,便聽見那人繼續言之:“也難怪,除非是慕淑妃或者高貴妃宮中的人,其他宮人啊怕是進不來這太醫院的。”
郭初祎此話說的确是事實,不止是這太醫院,現如今三宮九殿的所有人,皆是畏懼他話語中的這兩個人。
貴妃高欣顏,為這後宮之中數年,行事一向是心狠手辣。加上她的父親在朝中位居高位,便是更沒有人敢去得罪她了。
而淑妃慕瑾……于今年才步入衆人的視線之中,卻着實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三宮九殿中誰人不知,她懷着的是當今聖上的骨肉。得罪了她,更是沒得好日子可言的。 郭初祎如此想着,只得嘆了一口氣。叔父這些時日皆在奉皇上之命,給那慕淑妃開着調養身子的方子,如此大的擔子壓制在他的身上,也難怪不過區區數日,叔父便出了這麽多的白發。“你們在賢靈宮
,定要照顧好慕淑妃,不要枉費我們太醫院的這麽多人為了她腹中的皇子日夜操勞。”郭初祎如此沖着若荷說道。 他的語氣之中雖然有些嚴肅之意,卻是并無責備的,而若荷卻是聽得心下浮升了一種嘲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