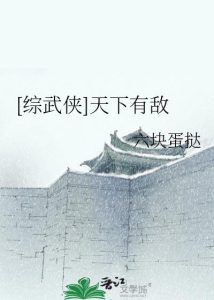一時間議論紛紛,衆人都覺得是個好辦法,步秋塵的尋人術乃是仙界第一,只是不知他願不願意幫忙了。
李茂歸看了眼步秋塵,恭敬問道:“可否請真神助我等尋找真正的殺人兇手?”
步秋塵并未直接回答,而是先看了看檀淩,檀淩微微颔首,步秋塵方才起身:“舉手之勞。”他先是去查看了下屍體,發現除了胸口的血洞之外,裏面的內髒并未缺少,這個瘡口足有拳大,駭人的很,所以從直觀上,以為是被掏了心肺。
步秋塵按了按他的胸口,心髒已無跳動,伸手去摸頸脈,也無浮動,步秋塵似是看到了什麽,撥了撥他的衣領,一個手印在喉嚨處,已呈現青紫狀。
步秋塵仔細看着這個手印,當時對方應當是掐着他的脖子,左側留下一個拇指指印,右側有三指,步秋塵皺了皺眉,分析道:“頸部指痕纖細,左側一指印,右側三指印。”
“啊?”難道是四肢手指的怪物?有人驚叫。
“不是,應當是女子所為。”鳳浔蔚笑了笑,以自己為例,掐了自己的頸項,衆人頓時明白了她的意思。
她的小拇指微翹,掐的正是蘭花指,所以大膽猜測,行兇者乃是一名女子。
步秋塵點頭,認同了鳳浔蔚的說法。
也不待衆人催促,步秋塵命人取了一塊白布,在死者的頸項上擦了擦,而後雙手在胸前合十平放,掌心輕輕揉搓,閉目念咒。合十的手掌漸漸發出水藍色的光芒,随着光芒的暴漲,步秋塵的周身都被這耀眼光芒籠罩。
手中白布沾染了兇手的氣息,通過此氣息來尋找兇手,無需在浩瀚六界尋找,只需在仙島搜尋,這些對已是真神之位的步秋塵來說簡直太容易了。
不消片刻功夫,他便已尋覓到那人微乎其微的氣息。
可下一瞬,氣息全然不見,步秋塵掌心猶如按着熱烙鐵,燙的他雙掌迅速開啓,掌心的白布已經化為一縷青煙漸漸消散。
“怎麽可能!”步秋塵失聲驚呼,不可思議的看着自己的掌心。
步秋塵耳邊忽然響起十分清晰的聲音:“沒有什麽不可能。”那聲音仿佛就像是在他耳朵裏響起一樣。
“怎麽了,真神?”李茂歸見步秋塵異樣,急忙問道。
“無事。”步秋塵以為自己幻聽了,擺手搖頭,又命人去取白布,還想再試一次。
“蠢鈍不堪……”這聲音猶如耳邊呓語,十分詭異。
步秋塵看向檀淩,檀淩對上他的眼神,似乎也發現步秋塵的不同之處,似是有些迷惘。
“小心身後!”檀淩恍然回神,步秋塵身後忽然出現一個模糊的輪廓,連忙示警。
步秋塵起手式擺出,踏出數步與那人保持距離,那人卻并未攻擊,只是站在原地,一席男裝,頭戴帷幕,令人瞧不清面容。
衆人立刻一縷神息探去,無功而返。
白芷瞧着如臨大敵的步秋塵,輕嘲着搖搖頭,不待他人發問,率先說道:“在座諸位修為不淺,難道就沒看出來,他本就是個死人嗎?”
竟是女聲,衆人驚訝。
她開腔,檀淩就已經聽出是白芷。
李茂歸如臨大敵問道:“你是何人?”
“吾為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吾手下成了替罪羔羊,被你們冤枉了,這事怎麽算?”說罷,已經一縷法術過去,硬生生将捆仙索斬斷。
衆人立刻明白過來,想必眼前不以真面目示人的這位來客,就是古容口中的主上了。
“姑娘,古容等人還未洗脫嫌疑,甚至是你,也在懷疑之內。”李茂歸拿出威嚴出來。
步秋塵只見過白芷兩三面,第一次匆匆一瞥,後兩次專心防備,無法根據聲音貿然猜中此人就是白芷。
步秋塵探究的看着她,猜測着她的身份,要在中皇山修建宮殿的人,不可小觑。
白芷也不辯解,指尖流出些許白霧,白霧緩緩鑽入屍體的鼻尖。
衆人已經坐不住,踮腳看着,那屍體忽然睜眼,撲棱一下,坐了起來。
也不知是哪個不着道的失态尖叫:“夭壽了,詐屍啦!”
修煉淺薄的立刻四散奔逃,做鳥獸散了,還有一些還算鎮定的,指尖掐符,就差按在屍體眉心了。
那‘屍體’先是轉頭将眼前狀況納入眼底,而後看向站在身邊的帷帽人。
“慌什麽!”步秋塵實在看不下去了。
李茂歸也忙出聲制止那些還在奔逃的人。
先前檀淩被他們的定論和消息先入為主,也沒去細看,只湊熱鬧的姿态,并未認真觀察過屍體。
原是一場荒誕鬧劇,檀淩下了定論。
白芷對着坐起身的‘屍體’撩了下帷幕,露了個角,‘屍體’立刻看到了真容,正是白芷,她十分淡漠的垂眸看了看他,那眼神裏浸透了寒霜,聲音低沉的猶如一把古琴,徐徐誘導着:“事情曲折你自己說吧,別冤枉了吾座下三人即可。”
‘屍體’哪裏敢冤枉了她的手下,站起身對諸人行禮:“敝人壇言,乃前任鬼界鬼君。”
諸人大夢初醒,紛紛交談,大多數人知道有壇言這麽個人物,但是鬼界與其他幾界并無來往,所以只聞其人而已。
“敝人不小心受了傷,關閉六識養身,未曾料想鬧出這樣大的誤會,實屬罪過。”壇言向四方衆人抱拳致歉。
衆人終于舒了口氣。
在座之人竟無一人發覺其只是關閉六識養身,實在是笑話。
這場鬧劇最終不慌而散,偌大的殿中眼下只剩下幾人。
白芷念着諸多原由,未曾深究鼎天宮冤枉古容等人,欲領人離開。
“尊駕請留步。”一直未曾說話的許溫說話了。
許溫走至她身邊,說道:“尊駕既是他們的主上,那我們不妨談談生意。”
檀淩聞言,皺了眉,審視着白芷。
已經離開的人被這場鬧劇鬧得估計忘記了,那個請鼎天宮在中皇山重建宮殿的人,正是此人。
白芷本想趁着此次東海仙市将東西收個八九不離十,眼下看來,還缺不少物件:“東西還未收齊。”
“無礙,随意談談。”許溫微笑。
白芷隔着紗看着許溫:“既然如此,那就去個可以談話的地方吧。”
“這邊請。”許溫說,引領白芷離開。
“且慢!”檀淩起身,三步并作兩步:“吾與她有話要說!”
白芷和許溫頓住腳步,回眸看去。
“我有話要與你說。”檀淩已難掩情緒。
白芷笑了,瞧瞧面前這個已經憤怒到極致的人。
“待我與許副掌門敘談過後,我們再敘也不遲。”她轉身再欲走,卻被檀淩扯住袖子,白芷重重摔袖,轉身走了,許溫深深看了檀淩一眼,跟了上去。
檀淩欲追,李茂歸走了出來,攔住去路,異常堅決的出聲制止:“這位神君,我鼎天宮歷來以築工為主,此事乃我鼎天宮內事,您實在不方便旁聽。”
步秋塵走上前來,搖了搖頭,示意檀淩有話可以一會說。
檀淩略一思忖,只得作罷。
因壇言而起的這場鬧劇散了,鼎天宮掌門李茂歸以養病為由,請壇言在鼎天宮暫住。
壇言致了謝,禮貌的退去了,被鼎天宮弟子領往客房,他胸口的血洞依舊駭人,鼎天宮來了醫者,為他診治,上藥,囑咐他好好将養,并十分隐晦的提醒道:“壇言公子,修行不易,萬望誤入歧途,跌入魔道。”
醫者離開後,壇言強撐着身體開了窗,風吹來一絲絲粘膩的雨腥氣,猶如他胸口周圍緩緩翻散的魔氣。
窗外大雨磅礴,天空中濃墨翻滾,雷霆不歇。
道道閃電劈下,好似誰在渡着天劫,屋裏昏暗,閃下時,方能瞧清屋內模樣,壇言回想起殿上,白芷掀開帷幕微露出的那一角詭妙面容。
她的面容大多隐在帷帽裏,被壇言看見的,只有一小部分,那樣低垂寒眸斂了大半的涼意,可即便這樣,壇言還是被她的眼神震懼到了。她在責罪,責罪他害的她的三名手下受這無妄之災,她在警告,警告他再次出現在了她面前。
壇言很不舒服,這樣冷的天氣,背上卻如千足蟲爬滿了脊背,冷汗涔涔。
壇言早已決定不再請白芷幫忙,卻不曾想為她惹了這般大的麻煩,後悔莫及也無用。白芷對樓西岳的前塵往事毫無興致,或者說,與樓西岳有關的一切是種毒,她知道不能碰,會上瘾,所以規避着不再觸碰。
聖意難測,如今壇言只想躲着白芷真神,她那副樣子,其實離癫狂只是一紙之隔。
此地不可久留,難保白芷秋後算賬,思忖及此,壇言也顧不得其他,想辦法遁走了。
許溫帶路,走向了一座高殿,殿下臺階一百零一階,拾級而上,于殿門前停下,殿前有座陣,環繞整座殿宇。
許溫做了個請的手勢。
白芷回眸望去,檀淩果然跟來,長身玉立于臺階起始處,靜靜的看着她,她無奈的搖搖頭,穿陣而入。
白芷随他入了內殿,殿裏十分空曠,唯有冰冷的鎏銀白虎獸在殿中央,虎獸雕的生龍活虎,十分逼真。
殿裏連桌椅凳子都無,并非真正待客的地方。
白芷目光四處掃看,發現頭頂有一鐵籠懸在空中,熙熙殺氣就在周遭,她斷定,許溫不善。許溫随意扶着白虎獸長尾,似笑非笑的看着她。許溫本是個俊朗青年,面容裏卻總夾雜着幾分譏诮與不屑,仿佛這世上,沒什麽能惹他入眼的,有些忿世嫉俗。
“來者是客,既是客,那便以真面目示人吧。”許溫的話直白的令人不悅,這便是他的‘待客之道’。
白芷冷笑,也不說話,掀下帷幕随意扔了,帷幕的輕紗翻飛落地,帷幕下的她馬尾烏雲垂,腰若約素,面若朝霞,灼若芙蕖。
此乃真絕色。
許溫驚愕的說不出話,深深呼吸幾次,調整心緒:“白芷真神……”
白芷到是十分淡定的點點頭,問他:“你認識我?”
許溫面容幾乎崩潰,眼角還含着晶瑩。
他失态了。
漸漸的,大殿之中回蕩着他幾乎癫狂的哭笑聲,身體也被哭笑帶的都動起來,白芷鄙夷的看着他,如同看着一場戲。
“我們認識嗎?”白芷覺得許溫有些魔怔……
許溫搖頭否認,幾分貪婪漫上心頭。
“我見過你。”許溫深吸口氣,冷靜下來補充,“無數次。”
白芷喃喃自語,似不太确定:“我好像沒見過你。”
許溫點頭不語,只是目光炙熱的注視着她。
白芷被他看的很不舒服,将思緒拉回正道,問他:“你師父是誰?”
鼎天宮周遭的防禦陣,許溫擅長的築工,許溫那對所有人的敵意與不屑,白芷都看在眼中,許溫的師父是……白芷只等着他給與确定。
許溫深吸了口氣,一字一句道:“家師,羽行君。”